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八卦、虚伪、争风吃醋,无数宫斗剧塑造了人们关于女性友谊的刻板印象,让人不禁怀疑女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友谊。
而在历史文献中,在文字被男性掌控的时代里,人们也难以看到记录女性友谊的文字。直到女性拥有了获得知识的权利,她们之间的友谊才通过书信和文学创作,生动地呈现出来。
女性情谊究竟如何确立,并从幕后走向台前逐渐成为主流的交际语境?
在交往了三十多年的好友病逝后,这个话题引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资深研究者玛丽莲·亚隆的关注与反思,并与另一位好友德蕾莎·多诺万·布朗合作完成了这本《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回顾西方世界女性友谊的发展历史,从被忽视、漠视、歧视到今天被正视、重视,女性友谊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份情谊,其实是坚如磐石且弥足珍贵的。

《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
[美]玛丽莲·亚隆 特雷莎·多诺万·布朗 著
张宇 邬明晶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男性代言友谊的时代
在玛丽莲·亚隆看来,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600年的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里,男性垄断了写作,几乎所有关于友谊的文献都与男性有关,“男性才是友谊的代言人”。在古希腊名为“会饮”的酒会上,男人们还会热情而严肃地谈论关于友谊的话题。

古希腊墓葬中描绘会饮的壁画
在亚里士多德以男性为中心的论断中,“一个灵魂寄居在两个身体里”的关系是一种完美而理想的友谊。他坚信有男性朋友的男人才能获得个人幸福,社会由男性之间的友谊维系。
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家普鲁塔克甚至说:“妻子不应该有自己的朋友,应该和丈夫拥有共同的朋友。”
事实上,中世纪时,超越家庭的女性友谊就已经在修道院这样的场所中出现了。离开了家庭圈子的修女可以学习拉丁文用以写作,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信件、回忆录,我们才得以看到她们之间相互依赖建立起的深厚的情感,哪怕在年龄或者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能够做修女的女性毕竟是少数,她们的友谊与她们一起被封闭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因而欧洲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女性友谊的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修道院之外,友谊的故事依然由男性撰写,也只关注男性主题,人们对女性的友谊持怀疑或否定态度。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甚至断定:女人的灵魂不够坚强,承受不了友谊这种“紧密且持久”的亲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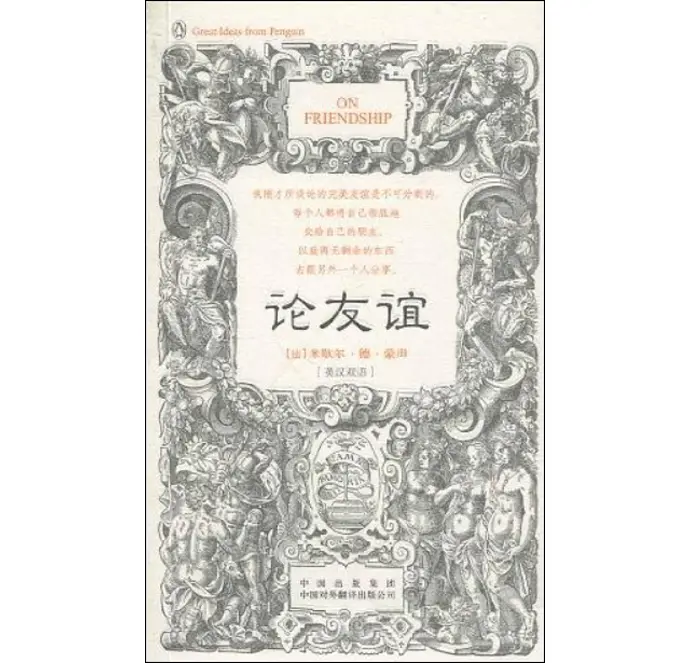
而就在蒙田还在世时,女性友谊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英国城里富裕人家的妻子,在经过丈夫许可之后,可以出门“拜访朋友,结伴同行,和同一阶层的人及她们的邻居闲话家常”。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为那个时代女性友谊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皆大欢喜》中的西莉亚和罗莎琳德,《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和海伦娜,《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尼莉莎,《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米温妮皇后和朋友宝琳娜……无论是出身宫廷贵族的女性,还是来自酒馆或乡下的下层女性,莎士比亚不仅确认了女性朋友的存在,还通过两个女人的合作来推动情节演进,迎来欢乐的大结局。
《莎士比亚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指出,莎士比亚对女性友谊的了解,很可能是从他母亲与他的姨妈的交往谈话中获得,他童年居住的小镇斯特拉特福德,是一个家庭妇女依靠邻居进行日常商业往来和相互支持的地方。

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底层女性不允许独自生活,1562年的《议会法案》和《工匠法案》,要求未婚女性要么服役,要么被送进监狱,于是,十几岁的女孩结婚前通常要在贵族家庭里服务四年,相同的处境与地位让她们彼此支持、陪伴,艰难度日中的交谈是她们发展友谊的支柱。
从17世纪开始,拿笔写作的英国女性越来越多,男性作品中缺乏的两个主题开始出现,一个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另一个就是作为朋友的女性。“我不是你的,而是你”,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她们也能共享一个灵魂。
肩并肩的女性友谊
在战争动乱中形成的友谊是人类所经历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之一,玛丽莲·亚隆认为这对女人也不例外,政治原因可以成为友谊的催化剂。
在十八世纪的美国,有一批愿意为共和政体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爱国女性”,她们抵制进口茶叶、抗议英国税收,还为军事防御筹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志同道合的女性主要通过书信联系,偶尔造访彼此的寓所,鼓励彼此成为“爱国与自由的理想模范”。例如出身政治世家的作家默茜·沃伦和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最初就是为了支持爱国人士而建立了友谊,通过书信交流思想近二十年。
华伦认为,政治不仅与男人有关也和女性相关,她在写给凯瑟琳的书信中说,“当这些观察是公正的,并且对心灵和品格怀有敬意时,无论是从女性的唇齿间流淌出来,夹在私人友谊的轻柔低语中,还是在参议院里由另一个性别的人大胆地说出来,都无关紧要。”
由于默茜生活在美国,凯瑟琳生活在英国,隔着大西洋的两个人仅在1785年前后有过一次见面交流的机会,更多的是通过书信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玛丽莲·亚隆不禁联想起当下网络友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果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两个人真的能成为朋友吗?“如果友谊的标志是感情和思想不断地交流,加上相互同情和尊重,那么凯瑟琳和默茜的友谊确实是真正的友谊。”
19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阶级女性也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有精力和时间去教堂或参加活动,在共同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她们自发成立了许多教会团体,为孤儿、穷人和未婚妈妈提供服务和帮助。这些团体迅速发展壮大成熟,她们按照“男性的议事规则”行事,不免引发了男性的担心——“一群女性竟然在没有男性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各种组织决策”。
玛丽莲·亚隆分析认为,大量女性走出家门、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些活动,并非对权力的渴望,真正原因是这些团体所提供的社交慰藉,让女性的友谊进入更广阔的世界。
在过去,出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的考虑而缔结的婚姻里,女人想从婚姻中得到陪伴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女人之间友谊就显得至关重要,她们进行心灵的沟通,讨论家庭事务甚至政治观点。
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斯坦顿与苏珊·安东尼的友谊,至今为人传颂。

单身的安东尼,与作为七个孩子母亲的斯坦顿,尽管生活环境不同,性格脾气也不同,但在反奴隶制、禁酒、主张女性权利方面的公共兴趣,让她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忠于婚姻与家庭的斯坦顿,在谈到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完全是一个整体,在我们所有的交往中,永远肩并肩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从来没有嫉妒的感觉”,即便有意见分歧、激烈争论,但是“互不理睬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小时”。
这段非凡的友谊超越了她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局限于“友谊的轻声细语”中,而是肩并肩地面向公众,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想——一种公民美德——提升到将女性纳入国家舞台的高度。
姐妹情谊
19世纪英美文化鼓励女性写作,书信文字中记录下了女性对于友情的看法,以及她们在婚姻中为友情争取空间而付出的努力。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写诗给将要结婚的女友:“我们悲伤地分开,因为责任/我的朋友,不久就会成为一位幸福的妻子”。当时的社会,相信女性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存在友情,“至少在合适的丈夫出现之前可以如此”。
结婚后的女性,往往由于繁琐的家庭事务而忽视了这段情谊,甚至遭遇丈夫的干涉。《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寄宿学校时就与埃伦建立了浪漫的友谊,38岁时嫁给了可以让父亲“晚年有个好帮手”的牧师尼克尔斯。

勃朗特在婚后写给埃伦的信中,除了对友人的深情、对文学的见解,还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抱怨、无法摆脱的烦恼。突然某一天,勃朗特在信中提及她的丈夫看到这封“太率性”的信,认为“非常危险”,他建议埃伦看过信之后就烧掉,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或者他要当“书信审查官”。埃伦不得不承诺看完信后就烧掉,但并未真正做到,于是才有了后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
“婚姻是友谊的葬礼”“婚姻是女性友谊的禁令”“婚姻妨碍了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的两件事……友谊和学习”,女性所经历的婚姻与友谊之间充满了敌意。即便是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小说《BJ单身日记》和美剧《老友记》也在讲述婚姻对珍贵的女性友谊的破坏。

受婚姻伤害的女性友谊,伴随着女权主义的浪潮,其价值一路上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姐妹情谊”成了女性友谊的代名词,意味着所有女性,无论有无血缘关系,都应该像对待姐妹那样,以爱和忠诚对待彼此。于是,当男孩与女孩约会,而使她取消与闺蜜的约定,这在政治上已不再正确;已婚的女人可以让丈夫在家看孩子,自己跟朋友去听摇滚演唱会。

女权运动对女性友情的影响重大,在过去,女性朋友被认为在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处于配角的地位,现在,她们在人际关系的版图上被标上了明确的位置。但女权主义所提倡的“姐妹情谊”由于忽视了社会阶层、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问题,这种人际关系仍然存在冲突。
如今,女性之间的友谊虽然不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具有政治光环,但它已然成为女性意识中的一股积极力量。“褪去了激进的、反男性的立场色彩,如今的姐妹情谊可能比五十年前更受欢迎,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强大”。
转载请超链接注明:头条资讯 » 被贴上塑料花、宫斗剧标签的女性友谊,历史上是什么模样?
免责声明
: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