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澳]唐納德·狄儂
摘編 | 徐悅東
眾所周知,著名畫家高更為了擺脫文明的喧囂,來到南太平洋的“伊甸園”塔希提島,醉心於“高貴的野蠻人”的生活,並創作出許多經典作品。毛姆以此為原型,創作出了名著《月亮與六便士》。不過,太平洋島民是“遺世獨立”的“高貴的野蠻人”或許只是西方人單方面的想象。其實他們也有著自己的文化。太平洋群島處在多個文明的交匯地帶,來自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的航行者給當地帶來了紛繁複雜的文化影響。鮮為人知的是,印第安文明甚至也與太平洋群島有所交流,這也打破了印第安文明“與世隔絕”的刻板印象。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劍橋太平洋島民史》,略有刪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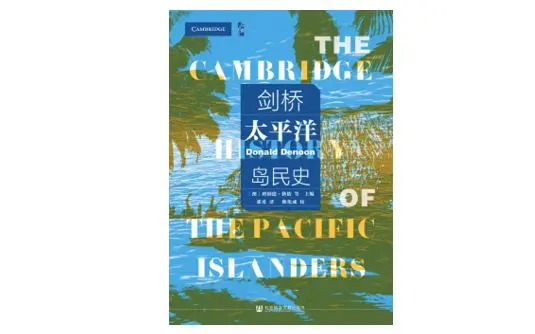
《劍橋太平洋島民史》,[澳] 唐納德·狄儂主編,張勇譯,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距今約500年時,歐洲人到來前夕的太平洋是怎麼樣的?
在距今1000~800年時,人類開始定居新西蘭北島和南島。在距今約500年時,隨著更為偏遠的查塔姆群島也被佔有,人類完成了對太平洋島嶼的殖民。雖然亨德森島、皮特凱恩島和範寧島(那些波利尼西亞的“神秘島”)等島嶼曾被人類定居或造訪過,但後來都被遺棄了。由於再也沒有島嶼可尋,以及東邊的南北美洲已被人類找到並與之短暫接觸過,殖民就停止了。
在距今1000~500年時,波利尼西亞實現了人口快速增長、農業擴張和集約化。夏威夷人清除了數千平方千米背風坡森林,並形成了集約型旱作農田系統,即在夏威夷大島及毛伊島部分地區對甘薯、麵包果樹和芋頭等農作物實行了垂直分區種植。值得商榷的是,人口擴張在歐洲人到來前是否已達到環境上限,人口趨向穩定還是衰退。儘管在夏威夷沒有發現確鑿證據,但拉帕努伊島民很可能確實引發了環境危機,在馬克薩斯群島也可能出現過這種情況。
環境對增長的限制也被用來解釋夏威夷群島和其他群島等級森嚴的酋長制。
舊觀點強調土地戰爭和酋長的軍事領袖身份是有限環境無法承載人口壓力的必然結果。新理論認為當地居民在社會制度形成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酋長間的競爭則是發展的動力。儘管我們在討論等級酋長制和國家興起時經常援引夏威夷群島,但其作為國家形成一般方案原型的地位仍有待確定。一方面與其他島嶼“原型”一樣,情況的特殊性也很重要。夏威夷群島在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島嶼中是最與世隔絕的。如果沒有通過貿易或索取貢品與其他“原始國家”或其他社會建立起固定聯繫,那麼其他社會就不會發展成為國家。
另一方面,湯加群島和薩摩亞群島恰好處於這種聯繫之中,這種聯繫主要起源於1000年前的祖傳體系,從包括斐濟東部島嶼在內的區域角度來看應被視為一個“世界體系”。直到波利尼西亞人在美拉尼西亞海洋島東端所謂“離島”上和在密克羅尼西亞某些島嶼上建立社區,這個“世界體系”的影響才被廣泛感覺到。這些波利尼西亞人更有可能是來自西波利尼西亞王朝衝突的難民,而非受到友好接待的幸運漂流者。
在新幾內亞島和美拉尼西亞海洋島的一些地區,距今1000~500年時的物質文化和聚落形態似乎與歐洲人剛來時所觀察到的大體相似,但是在此期間它們在所羅門群島部分地區和瓦努阿圖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諸如蒂科皮亞島及其鄰近島嶼等“波利尼西亞離島”上,它們在距今約750年時發生了顯著變化。在蒂科皮亞島的物質文化中,波利尼西亞元素日益突出,一些建築採用了西波利尼西亞的樣式,從西波利尼西亞直接輸入了石錛,還在從瓦努阿圖停止輸入陶器後出現了一些新型人工製品。

高更的《兩位塔希提婦女》
在瓦努阿圖埃法特島上有一座這一時期的酋長墓葬。根據口述傳統,墓主人是來自“南方”的羅伊·馬塔。他不僅控制了埃法特島的許多氏族,還開創了埃法特島酋長頭銜。在他死後,氏族代表們將他與人祭和“自願”人牲埋葬在一起。羅伊·馬塔被描繪成波利尼西亞移民,而且他的葬禮也令人想起西波利尼西亞酋長們。與此前相比,在這一時期人們更加依賴諸如螫刺鑽孔器和蜘蛛螺扁斧等貝殼工具,這表明物質文化引入了新元素,而且陶器生產可能停止了。在阿內蒂烏姆島的兩座酋長墓葬裡出土了一組類似的裝飾品,這印證了有關酋長葬禮的口述傳統。其中一座墓葬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300~400年時,骨骼分析表明墓主人是波利尼西亞人。在埃法特島以及瓦努阿圖和所羅門群島的波利尼西亞離島上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其他幾座墓葬遺址,這些墓葬遺址都有著類似的物質文化。
離島上講波利尼西亞語的島民,新喀裡多尼亞和瓦努阿圖語言中的波利尼西亞語外來詞,包括毛伊提基和湯加羅亞神等波利尼西亞文化英雄的當地神話,以及與“湯加人”交往的口述傳統,這些都表明在過去700年裡離島受到過波利尼西亞文化影響。交往的性質及影響各不相同。如今生活在所羅門群島倫內爾和貝羅納的波利尼西亞人有一些關於皮膚更黑的被稱為西提人的口述傳統。根據口述傳統,當他們從“烏畢阿”(可能是新喀裡多尼亞烏韋阿島西部)來到這裡時,他們發現西提人早就定居於此了。在和平共處一段時間後,雙方發生了衝突,最終西提人被屠殺。這一故事似乎可被這兩個島嶼語言中的“西提下層語言”所證實,從而表明這裡的確曾存在過一個與所羅門群島主島講所羅門東南語族語言的島民有關聯的族群。
考古學證據表明,馬西姆地區的庫拉交易圈、巴布亞灣的希裡交換體系和加羅林交換體系等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500年前,庫拉交易圈對新幾內亞島本土產生了更加強大的影響。68雖然口述傳統表明希裡交換體系形成於大約200年前,但是與密集沿海貿易相適應的聚落形態大約出現在1200~1500年前,並在大約300年前再次出現。到大約300年前時,加羅林交換體系東部島嶼已衰落。
直到20世紀30年代新幾內亞高地才與歐洲人建立直接聯繫,但是間接影響也許始於200~400年前甘薯的傳入。甘薯不僅使高海拔地區也能發展農業,而且作為一種旱地作物還進一步提高了早已發展農業的高地地區的生產效率。它最初由西班牙殖民者從南美洲移植到菲律賓,然後通過交換路線又由菲律賓移植到馬魯古群島和新幾內亞西部。儘管甘薯在新幾內亞低地地區從來都不重要,但在大部分高地地區卻是主食,並在20世紀仍在向高地邊緣地區傳播。庫克沼澤第五階段(距今400~250年間)的排水系統可能為種植甘薯進行過改造,因為灌渠的規模和式樣與現代高地西部的甘薯園圃相同。然而,戈爾森將這一階段解釋為苗床栽培的發展期,並將第六階段(距今250~100年間)視為甘薯引種時期。在採用新作物之後,對種植空間進行了優化,而且還在第六階段放棄了庫克農業遺址第五階段的2/3可耕地。到那時,始自第四階段的沼澤栽培技術已失去主要優勢。甘薯使豬群得到大規模擴大,從而支撐了高地殺豬業和交換圈,如恩加地區的蒂交換體系和哈根地區的莫卡交換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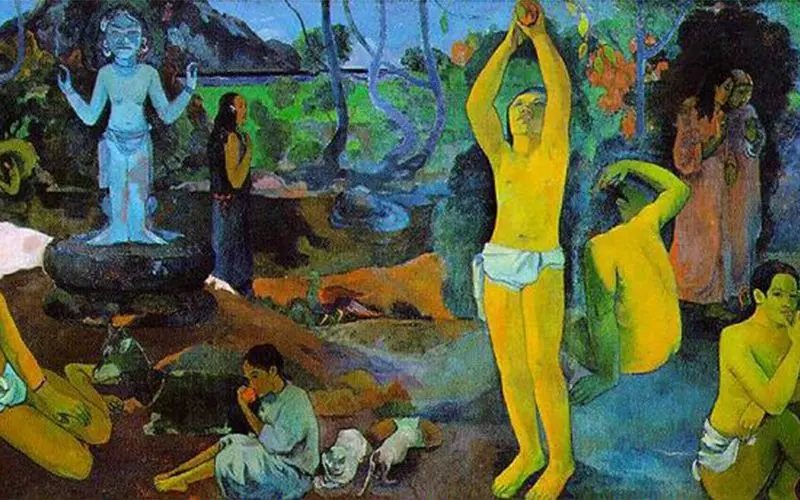
高更作品《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將到哪裡去?》
加羅林群島富饒的火山島不僅通過貿易彼此聯繫在一起,而且還通過庇護關係與低海拔的環礁聯繫在一起。在距今1000~500年時,密克羅尼西亞普遍出現明顯社會分層。馬裡亞納群島的拉提結構石柱是地位高者的住宅的地基,其歷史可追溯至約1000年前;波納佩島南馬特爾的巨石建築始建於750年前。南馬特爾由大約92座被狹窄水道隔開的人工小島組成,總面積為80公頃,其中小島面積僅為30公頃,島上有住宅、會堂和墓葬,都在高牆內。根據口述傳統,它是邵德雷爾王朝的首都。該王朝在波納佩島上建立了一箇中央集權的政權,直到距今大約1350年時才因低等級酋長叛亂而瓦解為五個政權。然後,南馬特爾基本被放棄。南馬特爾巨石建築開建時恰逢波納佩島製陶業終結。
距波納佩島480千米的勒魯島也有類似的“城市”建築群。勒魯島位於主島科斯雷島沿海,是一座人工擴建的小火山島。與南馬特爾一樣,島嶼中間地帶也有一個“非嵌入式的精英中心”,也由高牆內的住宅和會堂組成,也有運河網。人口在19世紀初約為1000~1500人,包括大酋長等科斯雷島高等級酋長。邁克爾·格雷夫斯將大酋長視為“酋長中的酋長”,而非絕對統治者,就像波納佩島邵德雷爾王朝那樣進行統治。他還指出,勒魯島的巨石建築要晚於南馬特爾,始建於公元1600年左右,但很快就完工了。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太平洋島民並不“與世隔絕”
到16世紀時,當地居民的大規模遷徙已完成。在通常描述“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合乎邏輯的分佈時,似乎這些文化區域不僅彼此不同,也有別於相鄰的澳大利亞、東亞和東南亞,或者美洲。這些術語的歷史和用法在第一章中曾被討論過。在這裡,我們試圖消除如下兩種印象:一是島上居民彼此斷絕了一切聯繫,二是整個地區在庫克時代之前一直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島上居民與世隔絕和孤立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存在的,但被18世紀的政治學家和哲學家誇大了。對於他們而言,島嶼社會例證了獨特的(和更加純粹的)原型。本文追溯了較小規模的居民遷徙和思想交流,年代通常要比上文所討論的更近些,從而以互動的證據糾正了與世隔絕和孤立的錯覺。
在長達2000年的太平洋史前時期,漂流者似乎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來自東南亞、南美洲以及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隻。每個島嶼都有大量漂流者。他們可能留下了一些可發覺的遺蹟,尤其是如果這些陌生人的身體或文化特徵明顯的話。在18世紀,一些歐洲人對島民體徵的多樣性留下了深刻印象,並推斷這肯定與東南亞的漂流者或殖民者有關。例如,拉彼魯茲在1787年確信東南亞人向東航行曾最遠到過薩摩亞:這些[波利尼西亞的]不同民族來自馬來人的殖民地。馬來人曾在不同時期徵服過這些島嶼。我確信,迄今為止在呂宋島和中國臺灣島腹地發現的捲髮人種是南半球的菲律賓、中國臺灣島、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瓦努阿圖、湯加等島嶼的和北半球的加羅林群島、馬裡亞納群島和夏威夷的土著居民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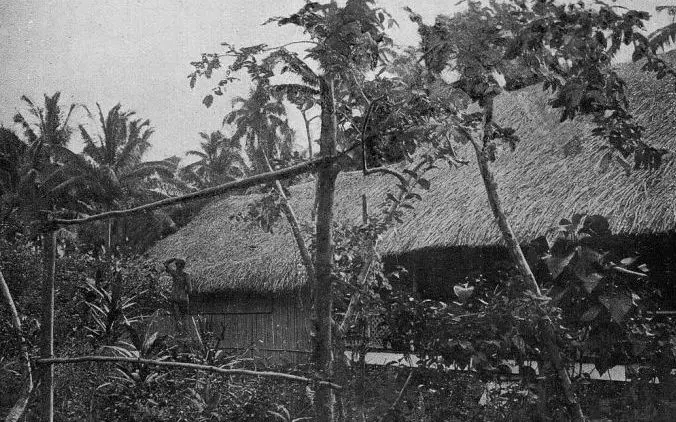
高更在塔希提島的房子。
在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和瓦努阿圖,他們沒有被徵服過;但是在那些更靠東的島嶼上卻被徵服了,因為它們太小了以至於無法讓他們從中心地帶撤退,於是他們就與徵服者混合在一起了……這兩個迥然不同的種族在薩摩亞群島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我想不出他們還有什麼其他起源。拉彼魯茲的觀點長期以來一直被用來解釋波利尼西亞人與斐濟人等美拉尼西亞人在身體特徵、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差異。
最近,學術界主流觀點已經開始轉向反對文化擴散說,因為它強調從本質上對種族進行分類,有時其闡述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現代學者更傾向於從地方適應和土著能動性角度來解釋多樣性,但是就像將洗澡水連同嬰兒一起倒掉那樣,他們不僅拋棄了文化擴散理論,還罔顧了歷史事實。如果我們以一種比其代表人物更具批判精神的方式重新審視這些學術成果,我們就可以恢復對島民經歷的流動性和文化多樣性的恰當判斷。從定居東波利尼西亞到16世紀歐洲人闖入,跨太平洋航行可能很罕見,但數百年來當地居民的確一直在太平洋邊緣航行。如果他們從未被拋棄在意想不到的海灘上,那將是非同尋常的。描述人類多樣性的現代遺傳學研究,重新喚起了人們對流動性的興趣。
在基督教時代開始之前,來自印度和中國的水手和商人越來越多地參與了東南亞貿易。隨著船舶變得越來越大和越來越適於航海,他們在異常天氣中(例如在厄爾尼諾現象發生時)有可能倖免於難,儘管其航程被迫終止。一份公元3世紀的中國資料所提到的外國船,長達50餘米,距離水面4~5米,可運載六七百人和250~1000噸的貨物。一份公元8世紀的中國資料所描述的船更大。在印度阿旃陀石窟,一幅公元6世紀的壁畫所描繪的一艘船,有三個高桅杆,一個裝有風帆的船首斜桅,複雜的操舵裝置,但沒有舷外支架。由於加裡曼丹島島民成功橫渡印度洋,定居馬達加斯加島,這表明了一些航行的規模。

波利尼西亞人
亞洲水手在太平洋上也很活躍。有證據表明,在史前時期至少有三艘東南亞船隻曾遭遇海難。富圖納島有一個關於中國人的著名傳說(中國在當地語言中被稱為Tsiaina)。Tsiaina肯定是在歐洲人到來後才有的一個詞語,但是似乎沒有理由懷疑這個傳說的主要元素。這一傳說被記錄下了六個版本。至少兩個版本都具有的共同要素包括:(1)這些移民曾在富圖納島的姊妹島阿洛菲島登陸;(2)他們在登陸後挖了一些井;(3)他們不僅與該島島民結了婚還生育了後代;(4)他們更改了一些地名;(5)他們一邊敲打被稱為拉利(lali)的木鑼,一邊四處走動,並根據回聲決定在哪裡定居;(6)他們推廣了更好的耕種方法;(7)他們推廣了經過改良的樹皮布製作方法和染色方法;(8)他們最終被推翻,並被屠殺。1843年到來的傳教士伊西多爾·格雷澤爾所編撰的富圖納語詞典將另外一個創新也歸功給了他們,即“moo”這個詞被定義為“據說來自中國的一種矮胖的豬”。
上述傳說的許多共同要素可以被證實。矮胖豬(moo)僅限於富圖納島及鄰近島嶼。71阿洛菲島上那個登陸點被稱為薩阿瓦卡,該地名在一些波利尼西亞語中被譯為“聖船”。挖井表明富圖納島當時正飽受乾旱之苦,因此這次航行可能受到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在薩阿瓦卡仍保留著一口被認為屬於他們的井,它深6米,寬2.4米。與歐洲人接觸之初,烏韋阿島和斐濟仍在使用木鑼“拉利”,但是直到最近它才在湯加和薩摩亞為人所知,這表明它們在太平洋中部島嶼上是新事物。利用水澆地種植芋頭是一個可歸因“中國人”的創新,因此波利尼西亞大部分島嶼都不懂這項農業技術。同樣,東波利尼西亞島嶼也不知道福圖納島樹皮布的兩種製作方法和一種染色方法。這些方法都被認為是“中國人”的發明。
富圖納傳說聲稱,那些“中國人”被推翻是因為他們的統治日益難以忍受。這似乎發生在荷蘭探險家斯考滕和勒梅爾於1616年訪問富圖納島之後(參見第四章),因為他們探險隊的一位藝術家描繪了島上酋長們的模樣,他們的頭髮又長又直,梳著辮子,而當地老百姓都是捲髮。這些荷蘭人還記錄了一個專門稱呼酋長的詞,該詞在傳教士到來後就逐漸被廢棄了。這個詞就是“latou”(準確拼法為“latu”)。該詞與許多東南亞語言中的“datu”是同根詞,意為“國王,國君,統治者”;薩摩亞語中仍保留著該詞的同根詞“latu”,意為“主要建設者”;斐濟語中也保留著其同根詞“ratu”,意為“酋長”;在一些湯加人姓氏中也保留著其同根詞。富圖納語中的敬詞也在傳教士到來後被廢棄了,但是,仍可找到一些痕跡,而那些湯加、烏韋阿島和薩摩亞仍使用的敬詞顯然與富圖納語有著共同的來源和聯繫。
20世紀20年代,學者E.S.漢迪認為,富圖納島的“中國人”可能也將湯加羅亞教帶到了西波利尼西亞,從而使之取代了那裡的印度-波利尼西亞人的宗教。據漢迪推測,湯加羅亞教起源於中國的華南地區。但是,由於湯加羅亞神在波利尼西亞被認為是“海洋之王”,因此上述宗教似乎更有可能與當地居民一起來自蘇拉威西島西北的桑義赫群島,“tagaloang”在那裡意為“公海、海洋”。其他波利尼西亞語詞語,包括木鑼“lali”,也似乎可追溯至桑義赫群島。此外,敬詞在這些語言中也很重要。桑義赫群島島民是傑出的造船匠和水手,由於他們的社會分化為貴族、自由民和奴隸,不禁讓人想起波利尼西亞那些受到湯加羅亞教影響的島嶼。
迄今為止,人類在東波利尼西亞定居的最早放射性碳年代是公元300年,遺址位於馬克薩斯群島努庫希瓦島。該遺址出土的陶器碎片明顯產自斐濟的雷瓦三角洲。馬克薩斯群島的首批定居者顯然是湯加人,因為馬克薩斯語中的某些詞語不可能來自其他地方,如“mei”(麵包果)、“maa”(麵包果醬)、“puou”(各種麵包果)、“too”(甘蔗)、“tokave”(各種小椰子)、“hoho‘e’Kuhliidae”(魚類)和“kumaa”(老鼠)。此外,馬克薩斯群島還有非湯加血統的定居者,具有美洲血統的定居者似乎是從拉帕努伊島(復活節島)來到這裡的。
拉帕努伊島可能早在第一個千禧年中期就有人類定居了。太平洋學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這裡的首批居民是波利尼西亞人。(語言學家將東波利尼西亞語言分成兩類,即馬克薩斯語和塔希提語,而拉帕努伊語則被認為是單獨語種。)然而,首批拉帕努伊島居民更可能是厄瓜多爾或秘魯的美洲印第安人,因為在歐洲人到來時拉帕努伊島和東波利尼西亞其他島嶼上種植著大量美洲農作物,特別是甘薯、菠蘿、辣椒、26條染色體的棉花、無患子和木薯。從亞洲傳入南美洲的葫蘆、香蕉和藍蛋雞也一定是從東方傳入東波利尼西亞的。
在此後數百年裡,漂流者顯然是帶著一些農作物和雞從拉帕努伊島漂流到馬克薩斯群島、皮特凱恩島、曼加雷瓦島、土阿莫土群島和社會群島。起初,這些是東波利尼西亞經濟的重要內容,但是由於波利尼西亞人從西部引入了芋頭、山藥、甘蔗、麵包果樹和構樹等農作物,擁有這些農作物的島嶼幾乎遺棄了辣椒、菠蘿和棉花,但是甘薯、葫蘆和香蕉仍然很重要。鬥雞和一種被大量飼養的家禽也從西波利尼西亞引進到東部,此外還有狗和尖背豬。許多東波利尼西亞詞語,包括一些與香蕉和雞有關的詞語,在西波利尼西亞並不為人所知。這表明該地區的早期文化融合了東方和西方的特色。其中一個特色似乎應完全歸因於美洲的影響,即建造大型石頭建築,如土阿莫土群島和社會群島的會堂或宗教庭院。然而,會堂(“marae”)一詞肯定來自西方(在富圖納語中,“malae”意為“公共場所”)。

波利尼西亞的航行者
大約在公元1100年時,拉帕努伊島成為第二支美洲印第安人移民的家園。他們屬於以安第斯山脈為中心的蒂亞瓦納科文化。他們及其後代在拉帕努伊島建造了著名石像摩埃(moai)和小型塔式建築物圖帕(tupa),後者在名稱、外觀和功能上都類似於安第斯山脈的儲爾霸(chullpa)。所有幸存的圖帕都被建造成以承材支撐的拱頂,即內牆石材從底部到頂部相互重疊,從而使直徑越靠頂部越小,直到形成圓頂狀天花板。另一獨特之處是把大楣石置於小而低的入口上方。在安第斯山脈,儲爾霸始建於公元1100年,停建於西班牙徵服美洲時期。
拉帕努伊島的圖帕極其類似於安第斯山脈的早期儲爾霸。這兩個地方的建築物都被認為是用來陳列死者骨頭的。曼加雷瓦島附近的特莫埃環礁有一個類似圖帕的會堂,叫作奧圖帕(Otupa)。另外,拉帕努伊島的摩埃和圖帕的建造者似乎對波利尼西亞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社會群島的口述傳統講述了一個關於“羅圖馬王子”的故事。這位王子定居博拉博拉島,並通過婚姻成為王室成員,其子孫到19世紀中期時已在該島延續了九至十四代。社會群島其他史前外來者都來自失事的西班牙輕快帆船“聖萊斯梅斯”號。
該船是1526年5月26日從麥哲倫海峽進入太平洋的四艘船之一。六天後,“聖萊斯梅斯”號在一場暴風雨中與船隊失散,該船及其約53名船員從此杳無音訊。這些船員有來自加利西亞和巴斯克等地的西班牙人,還有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佛來芒人。1929年,在土阿莫土群島阿馬努環礁上發現了四門古代大炮,其中兩門鐵定來自“聖萊斯梅斯”號。這艘輕快帆船夜間在阿馬努環礁擱淺,船員們扔掉大炮,繼續向西航行,尋找避風港修理該船。他們的第一站是塔希提島以東400千米處的阿納環礁,一些船員在這裡離開了該船。其餘船員來到塔希提島西北約200千米的賴阿特阿島東南角的奧波阿灣,於是他們開始在這裡修理這艘輕快帆船或建造了一艘新船。在這項工作完成後,他們冀圖向西南航行到好望角,然後前往西班牙,起航前留下了一些西班牙人,同時帶走了一些波利尼西亞男人、婦女和兒童。
文化傳播論者推測,來自一艘在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上失蹤的西班牙大帆船的漂流者對夏威夷產生過影響。這個理論起源於庫克船長抵達夏威夷之後不久。三件重要物品使他的幾名軍官確信西班牙人早於他們抵達這裡。這些物品是夏威夷酋長的羽冠頭盔和羽飾鬥篷,還有幾把鐵匕首。軍官詹姆斯·金認為頭盔和鬥篷與波利尼西亞風格“截然不同”,並聲稱它們與以前的西班牙風格“非常相似”。一些在19世紀初被記錄下來的夏威夷口述傳統支持了詹姆斯·金的假設。其中一個版本講述了七名白人男子在庫克船長到來之前是如何登陸凱阿拉凱誇灣的。據說,他們的後代不僅“膚色較淺”,還有“相應的棕色捲髮”。
在20世紀,對西班牙親戚說的質疑越來越多。一位批評家指出,夏威夷酋長的頭盔與16、17世紀的西班牙頭盔大不一樣。然而,據悉在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之間曾有過三艘西班牙大帆船失事(分別在1576年、1578年和1586年)。20世紀50年代末,在凱阿拉凱誇灣的一個洞穴裡,曾發現一位被奉若神明的酋長的墓葬,並在棺木中找到兩件非波利尼西亞風格的物品。其中一件是嵌在木柄上的一塊鐵,像鑿子;另一件是一段機織帆布。也有人認為,夏威夷頭盔模仿的是菲律賓耶穌受難復活劇中扮演聖經時代羅馬士兵的演員們所戴的頭盔。
同一時期另一艘失蹤的西班牙船似乎是在所羅門群島的波利尼西亞離島翁通爪哇環礁結束航行的。這就是“聖伊莎貝爾”號。它是1595年離開秘魯駛往所羅門群島的門達尼亞探險隊的四艘船之一。“聖伊莎貝爾”號在接近目的地時與其同行船隻失散,從此杳無音訊。1971年,在聖克裡斯託瓦爾島(今所羅門群島馬基拉島)的帕穆阿發現了一些外來陶器碎片和其他獨特物品,這表明有船員和乘客曾在那裡宿營過。由於翁通爪哇環礁有許多具有歐洲人相貌的島民,因此自那以後就一直表明“聖伊莎貝爾”號後來擱淺在那裡。其他具有類似相貌的翁通爪哇環礁居民已經遷至霍尼亞拉和聖伊莎貝爾島。
另外三艘失蹤的西班牙船隻,以及一群被困馬紹爾群島的叛亂者可能在密克羅尼西亞也扮演了類似角色。1527年,“聖地亞哥”號和“埃斯皮裡圖桑託”號在從墨西哥遠航摩鹿加群島(今馬魯古群島)時失蹤。這兩艘船連同60名船員似乎失事於加羅林群島西部的法斯島和烏利西環礁。在將近70年後的1595年,門達尼亞探險隊的輔助船“聖卡塔利娜”號可能曾靠岸加羅林群島東部的波納佩島,這艘滲漏嚴重的船最後一次被看到是在波納佩島附近。在這之前的1566年,27名“聖赫羅尼莫”號船員在譁變失敗後被放逐到馬紹爾群島最西端的烏傑朗環礁。
漂流者影響的全部性質和程度永遠不會被確定。與大多數史前史學者相比,這種說法所考慮到的漂流者要多得多(也更多樣)。除了外來的漂流者,美拉尼西亞人也從一個島嶼漂流到另一個島嶼,波利尼西亞人和密克羅尼西亞人也是如此。進一步研究可能會還原其中一些水手的本來面目,但這些驚人的新發現只是漂流者參與太平洋島嶼定居和移居故事的一小部分。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宮照華
校對 | 李項玲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歐洲人到來之前的太平洋島民,並不是高更眼中的“高貴的野蠻人”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