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後商
在2017年雅布提獎長篇小說類一等獎作品傳記小說《馬查多》(Machado)中,巴西作家西維亞諾·桑提亞戈(Silviano Santiago)回顧了巴西文學大師馬查多·德·阿西斯最後四年的生活,他的藝術、孤獨和癲癇病。行將終老的阿西斯,在兩名女傭的幫助下,努力和癲癇症共處,與此同時,巴西第一共和國對中央大街開始了現代化的改造——就在不久前,阿西斯還被調到了工業部。私人生活和歷史變遷彙集於《馬查多》,阿西斯渴望成為現代人,但又是以保守的、不公正的方式。例如,阿西斯從社會意義上否認自由勞動的存在,但又從本然意義上不聲張地反對奴隸制,阿西斯的矛盾恰恰是一個典型。

馬查多·德·阿西斯,1839年生於裡約熱內盧,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巴西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頭像被印在面值一千的紙幣上。1897年創辦巴西文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生前身後發表了眾多作品,涵蓋了全部文學體裁,共計十部長篇小說,二百零五篇短篇小說,以及大量詩歌、戲劇作品,代表作有《沉默先生》《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金卡斯·博爾巴》等。
1.文學上的世界主義者
阿西斯生於1839年,是混血人油漆匠和白人洗衣婦的兒子,其血統中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但他一生都在努力隱藏自己的黑人身份。他的教育生涯很短,只讀過小學,他的啟蒙來源於一位拉丁神父和刻苦的自學。有資料可查,阿西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是《窮人刊》上的一首十四行詩。阿西斯的職業生涯從國家印刷局起步,此後又先後做過校對員、編輯、撰稿、主編助理等——為報刊等媒體撰稿是阿西斯堅持一生的事業。三十多歲的阿西斯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彼時的巴西還是佩德羅二世治下的巴西帝國,尚未廢除奴隸制。阿西斯先後在農業、商業、公共工程部履職,官至公共工程部局長——考慮到拉美文人的政治色彩,這種行為並非迂腐的表現。
在文學方面,阿西斯無疑是一個世界主義者。在文學譜系上,他有屬於自己的位置,但沒有那麼明晰——他分頭吸納了巴洛克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歸根結底,他使自己面對了諸多經典“問題”,面對那些永遠都不過時的“問題”。阿西斯不拘泥於類型,他寫詩歌、短篇、長篇、戲劇、評論等等,且以一種現代又古典的方式雜糅了諸多弱類型。在宗教、政治、文學、生活等方面,阿西斯的思想是自由的,近乎無政府主義的。阿西斯的作品所顯示出來的懷疑色彩,並不是存在主義式的,而是後巴洛克式的——於他而言,絕望和希望是一個詞。阿西斯是隱藏式的他者,又是神秘化的自我。作為一個隱藏式的他者,他有著洞察事物和走入讀者的可能;作為一個神秘化的自我,他召集著他所書寫的事物和思想。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阿西斯的每個段落簇——看得出來,阿西斯的作品是累進式的,是夾雜著空白的——都會讓作為讀者的我們平靜下來,讓我們追隨他的敘述成為更真實的自我。
2.文學的本質是人的普遍意義
“我過著半隱居的生活,偶爾參加一次舞會,去去劇院,或聽演講,但大部分時間是我獨自度過的。我活著,任其事業和光陰流逝;在奢想和失望中時而心緒不寧,時而心灰意懶。我撰寫時政文章,從事文學創作,向報刊寫文章或詩篇,竟然還得了個善辯和詩人的美名。當我想到已當了議員的羅伯·奈維斯和侯爵夫人維吉麗亞,我自問為什麼不能成為比羅伯·奈維斯更好的議員和侯爵。‘我更有價值,比他的價值大得多’,我望著鼻子尖說了這番話。”阿西斯在其經典《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中如是自我剖析。
貴族布拉斯·庫巴斯在其死後懷舊憶往,也邀請我們體味他雍容又枯燥的人生。他偽裝成斯特恩的巨人,但更偏狹,更執著於高貴又可憐的感情、優越又懊悔的腔調。本書的喜劇效果幾乎是一種古典文學變形後所產生的,不過,阿西斯在處理喋喋不休和快速切換的時候,顯得更為剋制和有所保留,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對象是世情的可笑和人的多變,而不再是巴洛克式的半虛構世界。布拉斯·庫巴斯,或者阿西斯總是在節外生枝,總是變了面具,變了情感,變了指向,透過那些自命不凡、脆弱的表演、各一半的快樂和憂鬱——“我是人,我的大腦是個舞臺,上面演出各種劇目,神聖、嚴肅、活潑的話劇,高雅的喜剛,形形色色的鬧劇、悲劇、滑稽劇。”在這之下,是在愛情和事業上遭遇重重挫折和失敗的布拉斯·庫巴斯。這個故事既不輕鬆愉快,也不狡猾骯髒,而是帶著笨拙的平衡,有如新生。這位死去的作家在死亡之後開始了他最本真的書寫,這個遊戲講的是作家的自由。
在某種程度上,阿西斯是失敗的,因為他從未真正實現預想的在地性嘗試,或者某種現實主義的效果,在這一點上,他比不上巴爾扎克之類的典型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擁有現實主義的所有元素,甚至更歐洲、更古典,但它幾乎沒有焦點,無法被一個確定的類型所統攝,缺乏一種整體的美感——阿西斯過於隱藏其意圖的、過於書面的、獨特的反諷加劇了這個結果。從中,我們還能發現他的自戀、他的注意力缺失症、他的對經典的依賴、他的藝術上的強迫症。蘇珊·桑塔格所認為的阿西斯的成功正是基於上述的失敗,潛在的失敗,於是阿西斯把自己安置在一個古怪的位置,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巴西現實角度、現代主義文學角度等等——阿西斯總是輕易超越了這個想象所能承載的一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人士的過度成功幾乎總是一種更大的偏執、更存在主義的言說,這也是為什麼桑塔格認為貝克特部分失敗的原因。
典型的說法是,阿西斯沒有提供給我們一種真實的巴西,無論是巴西的自然風光,還是巴西的歷史狀況,後者最重要的例子是他對巴西的蓄奴問題避而不談,而巴西是全世界最大的蓄奴國,而它直到1888年才廢除奴隸制,是最後一個廢奴的國家。就此而言,阿西斯對於現實問題是採取退讓態度的。1873年,阿西斯發表《巴西當代文學的創新:民族性本能》一文,提倡民族主義只是文學的一隅,文學的本質是人的普遍意義,這才是真正的“巴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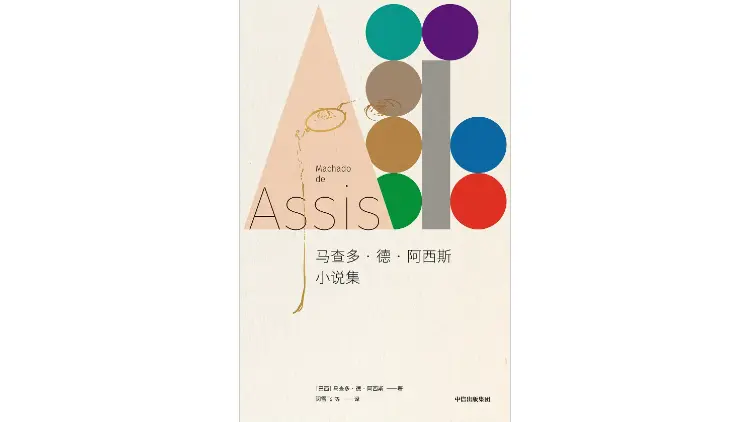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作者:(巴西)馬查多·德·阿西斯,譯者:閔雪飛,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7月
3.阿西斯代表著巴西真正獨立的一代
阿西斯帶我們回到了不確定年代的巴西,回到了已然的巴西。在他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中,故事被拉前,他的角色幾乎都存在於早於他的歷史時期,並且這些人物的感受方式也幾乎總是古老的,原始的,乃至於過於精緻的。然而,阿西斯仍然帶著他的角色狼奔豕突,將他們帶到歷史的舞臺之上,或者讓他們徵服整個歷史。對於最後的獲勝,阿西斯是深信不疑的,因為他是佈局謀篇的人,更因為他是世界文學的學徒。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的第一篇《精神病醫生》發生在“搖鈴宣告”的時期,負責搖鈴的人走家串戶,收羅所在地的信息,最後他會將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將信息公佈給所有人。伊塔瓜依當地的醫生西芒·巴卡馬特相信科學的精神,他的信條是“科學也毫不例外,它是項天天不斷探索的事”。他發現了醫學裡一個未被開發的領域,精神病學,它曾經是一座孤島,現在被醫生證明是一座大陸。精神的健康才是醫生最值得尊重的事業,西芒·巴卡馬特醫生如是說:“人的精神是一個巨大的蚌殼,我的目的是從中取出珍珠。”醫生將病人大致分為兩類,暴躁病人和溫順病人,然後再細分……在後來的治療中,病人會按照自己所患病的類型接受診治,諸如誠實病、忠誠病等。西芒·巴卡馬特為了收治病人,建造了綠屋,顧名思義,綠色的屋子,是當地最為豪華的宅子,後來還得到了擴建。
綠屋建成之後,西芒·巴卡馬特就收治了很多病人,諸如愛修辭學的年輕人、施捨錢財的科斯塔,甚至於他的夫人艾娃麗絲塔。由於醫生的“荒謬”的收治行徑,人們團結在理髮師波菲裡奧的周圍,進行了一場針對綠屋的叛亂,“玉米粥叛亂”。叛亂影射了巴西歷史上一次未成行的叛亂,蒂拉登特斯(Tiradentes)率領下的“米納斯密謀”(Inconfidência Mineira),只不過前者成功了。但旋即,發生了復闢。西芒·巴卡馬特的聲望在政權更迭時期達到了高峰,綠屋也藉機收治了鎮長和議員,但旋即,綠屋裡的病人都被釋放了。新的治療方案和立法方案得到了實施。故事的最後,取得了智識和精神雙重平衡的西芒·巴卡馬特離開了人世,葬禮很有排場。
《精神病醫生》的故事是多維度的,你可以說它講的是精神病的發現,也可以說它講的是科學至上只會帶來巴士底獄般的荒唐,也可以說它講的是政治的黑暗和翻覆,諸如此類。最重要的是,故事從不止一種發生的方式,它是關於故事的故事學,關於類型的類型學。在資料和素材方面,阿西斯從未逾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但在寓意方面,阿西斯是完全普世的。阿西斯的一個信念是,在社會和人的戰役中,勝利的總是社會,正如《精神病醫生》所昭示的。社會的勝利沒有看上去那麼令人不堪。在阿西斯的另一本小說中如是寫道:“這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但我們別無選擇。如果你沒有下決心要改變它,那就只能承受這一切,在這個社會裡照常生活。”最順從的人,像西芒·巴卡馬特醫生那樣,或許才是最瘋狂的,他們竟然將日常當作病態。
阿西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保守的懷疑主義,它既有道德的維度,又有美學的維度。在道德維度上,阿西斯是超然的、成熟的。比如,他反寫的《亞當和夏娃》一樣,《聖經》中的美與純潔不過是更大的邪惡而已,而我們所需的是更大的美好,是真正的上帝。再比如他借人物之口對“人性主義”的呼喚,帶著雙重的意味,“請求助於人性主義,它是容納精神的偉大胸懷,是永恆的大海,我潛入海底去撈取真理。”在美學的維度上,阿西斯代表著巴西真正獨立的一代,他徹徹底底地將那些原本屬於西方、屬於宗主國的文本改造成了新的文本。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種新的古典主義,新的現代主義。阿西斯是反歌德的,又是和歌德相對應的。他的懷疑主義還沒有抵達虛無主義,出乎啟蒙世界也沒有多遠。
早在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發表《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之前,阿西斯就做出了驚人的食人主義的實踐——在西方世界之外尋找更好的天堂。“只有純粹的精英成功地實現了肉慾的食人,它在自身內部承載著生命的至高意義,避開了弗洛伊德指定的一切疾病——教義問答的疾病。”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如是說。吉爾貝託·德·梅洛·弗雷雷(Gilberto de Mello Freyre)後來在《主與奴》(Casa-Grande & Senzala)為混血人所做的證明正是一個起點。而現在,阿西斯那張有鬍鬚、顯赫的、混血的畫像出現在紙幣、郵票、巴西文學院。
作者|後商
編輯|張進
校對|李世輝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馬查多·德·阿西斯:最順從的人,或許才是最瘋狂的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