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的道德评判抹除了一个人真实的处境
///
身为女性,要承受多少流言和恶意?
在第50届布克奖获奖作品《送奶工》中,北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创作了一个18岁女孩被“送奶工”跟踪的故事。而跟踪的原因,仅仅是女孩喜欢边走路边读书。令人愤怒的是,她被跟踪的遭遇非但没有得到身边人的帮助,反而被人谣传为不堪入目的私情。
母亲的斥责、姐夫的诋毁、邻里的议论纷纷里……女孩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区、所处的时代……这一切境况都通过“我”的视角折射出来,安娜·伯恩斯用粗粝的、口语化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压抑的世界,这个世界允许一个人对另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施压”。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书评人Laura Miller认为,《送奶工》传达了一种政治恐怖和性监视,它们共同加剧了年轻人的幽闭恐惧症。
“我们义不容辞地为你列举你的恐惧,以免你将其遗忘:物资短缺;过分依赖;古怪;不可见;可见;羞耻;被回避;被欺骗;被欺负;被抛弃;被打;被谈论;被可怜;被嘲笑;被认为又是‘孩子’又是‘老女人’;愤怒;其他人;犯错;凭直觉知道;悲哀;孤独;失败;失去;爱,死亡。如果不是死亡,那就是活着——”
从出生到死亡,从死亡到活着,书中所描述的恐惧并非特例,而是错乱、暴力与动荡的时局中,聚焦于每一个个体身上的时代境况。《送奶工》不仅仅是关于特定地方和特定时期的小说,也是一场在普遍意义上对社会危机进行的探索。安娜·伯恩斯用打破线性时间的句子挑战了传统的思考方式,尖锐地描摹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遭遇。整部小说用第一人称的意识流的叙事方式,刻画出荒诞的集体谣言下沉重的压抑感,但压抑的感觉之中又似乎想要开启什么,想要让人看到这个时代,看到这个时代下人性的境况,人的处境,人与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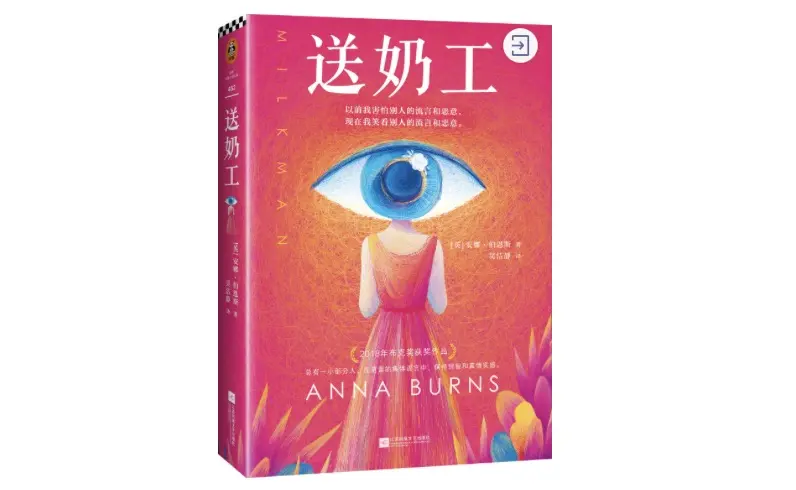
《送奶工》
[英]安娜·伯恩斯 著
吴洁静 译
读客文化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
新京报·文化客厅NO.47,我们联合读客,邀请到诗人胡桑、作家邱华栋,解读布克奖获奖作品《送奶工》背后的政治隐喻,思考荒诞的集体谣言下的女性困境。

胡桑
诗人,译者,文学批评家。著有诗集《赋形者》,诗论集《隔渊望着人们》,译有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奥登随笔集《染匠之手》和洛威尔诗选《生活研究》。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邱华栋
小说家,诗人。出版各类文学作品近百种,合计八百多万字。曾获中国作协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北京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林斤澜小说奖优秀作家奖等三十多个奖项。
01
去“标签化”
《送奶工》首先是一部虚构文学作品
在#METOO运动兴起的2018年,布克奖的入围名单里有不少重量级作家的作品,最终,组委会决定颁给《送奶工》这一具有实验性的女性主义作品。这显然是个大胆的决定,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在活动中,嘉宾邱华栋认为,出于种种原因,公众关注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不自觉地把目光偏向它延伸出来的社会话题
(如#METOO运动)
。毋庸置疑,从社会学层面对本书做女性主义解读,也是理解本书的重要角度。但阅读《送奶工》,首先还是应从它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来看待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态度;首先要认识到它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作品,并非纪实类小说,更不是新闻报道。从文学角度讲,它的美感、叙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的力量,这些东西是我们来看待这个作品,进入这个作品的大门和窗户。
《送奶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叙事视角,叙事主人公只有18岁,整部作品都是以一种类似于独白的方式,用第一人称讲述的,主人公的声音贯穿了始终。

《简爱》剧照
作者安娜·伯恩斯在书写中使用的是一种北爱尔兰腔的英语,带有一定地域性,其中还包含许多北爱尔兰的方言。我们知道像爱尔兰、北爱尔兰人一贯以彪悍著称
(在美国还有爱尔兰黑帮)
,所以从语言上来讲,他们说话具有一种独特的粗粝感。虽然作者是一位女性作家,但整部小说的语言读上去也非常豪放、具有力量。小说中,男人会经常用方言里一些非常粗鲁的脏话来骂女人,这种异常激烈直接的语言暴力,在主人公“我”心中激起很大的震动,也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外在击打力量。
对于《送奶工》这种口语化的叙述语调,胡桑也表示认同。他认为小说的故事性不是很强,但文学特征却十分独特,不同于现代主义巅峰期时在形式上探索的那种文学性,《送奶工》更多地深入到了当代历史,尤其是北爱尔兰历史的特殊语境里 。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是没有名字的,小说也没有表明明确的地域和历史背景,但仍能从女孩“我”的生活环境中、从“我”被跟踪的境况中,感知到“不安全”的表征。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小说里有一个词,英文叫mural, 中文可以翻译为“墙上的装饰画”“墙上的绘画”,分别出现在小说第二章和第七章。它其实指的是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以及周边一些城镇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在大街小巷的房子的侧面会画上各种各样的广告、新闻、事件、政治人物、口号,代表当下的某一种时代信息。这个词的出现,其实也暗示了小说的背景是在北爱尔兰,尤其是作者安娜·伯恩斯的故乡贝尔法斯特附近。而小说设定的1970年代,正处在“北爱尔兰动乱”
(the Troubles)
时期。
02
“没有名字”的人物
滥用权力剥夺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和可能性
胡桑介绍,北爱尔兰广义上属于爱尔兰,《送奶工》小说里经常出现 “边界”一词,常用“海对岸”、“马路对面”来表示与己方不同的对象和区域。
如果从历史和地理位置上联想,爱尔兰海对岸的岛屿,其实就是英国本土英格兰。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而英国是新教国家。虽然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和宗教的具体仪式上却有很大差异。小说里面也描绘了各种各样对于这种差异的划分,比如:“我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划分带来了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力的滥用。这种权力滥用弥漫在整部小说里面,也是这部小说想试图批判的。
小说中城镇的街区会被各种武装力量,划分成各种片区,两个社区可能就是两种政治力量。各种各样的政府的和反政府的武装会有“禁用的人名列表”,“社区的灵魂人物通过按时复审,决定哪些名字可以用,哪些名字不可以用”,这造成了小说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几乎所有人物都是没有名字的,包括主人公“我”和送奶工。
送奶工后来说“送奶工”就是他的真名,一个职业的名称便是名字,这是真的吗?没有人知道。而小说中为数不多出现名字的人物,又仿佛被名字符号化,比如歌手米莉·寇文顿,因为一首名叫《只有女人流血》的歌而著名,还有一战时期混迹于巴黎的脱衣舞女玛塔·哈丽,她被人们用来指责主人公“我”,说“我”像玛塔·哈丽,意味着不检点。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名字本代表着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但是小说中政治权力甚至介入到每个人的名字的使用之中,剥夺着每个人存在的可能性和独立性。
与权力滥用相伴随的还有暴力。胡桑认为,这部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关于性骚扰的小说,但它背后隐藏的更大的问题是:之所以会存在这样不正常的被性骚扰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暴力横行的社会。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其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里,阐述了三种束缚性的权力:一种是家庭,一种是绝对主义的国家,一种是绝对主义的教会。
小说中主人公“我”的母亲,就代表着家庭的权力。因为父亲是忧郁症患者,所以母亲在家庭中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她处处告诫“我”要信守婚姻的承诺,不要做“依附的女人”,女人要获得合法地位,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和一个普通男人结婚,履行生活中的普通职责。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挺实在的,但通过小说的叙述,我们会发现女性一直被各种各样的力量给规训着,哪怕是“做一个普通女人”,其实也是政治暴力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体现。
在母亲眼里,“我”变成了一个无法沟通、游离于社会、自由散漫的女人,变成了社区的出格者,只是因为“我”做了许多具有独立意义的事情,其中最关键的行为,就是边走路边读书。
03
“日落时的不安”
道德评判经常会抹除一个人的真实处境
胡桑表示,在《送奶工》中“边走边读”并非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读书癖,更象征着“我”面向自己的独立思考。主人公渴望通过阅读各种世界名著来获得一种辨认爱人形象的力量,塑造自身关于世界的一种想象,一种希望,一种未来,尤其是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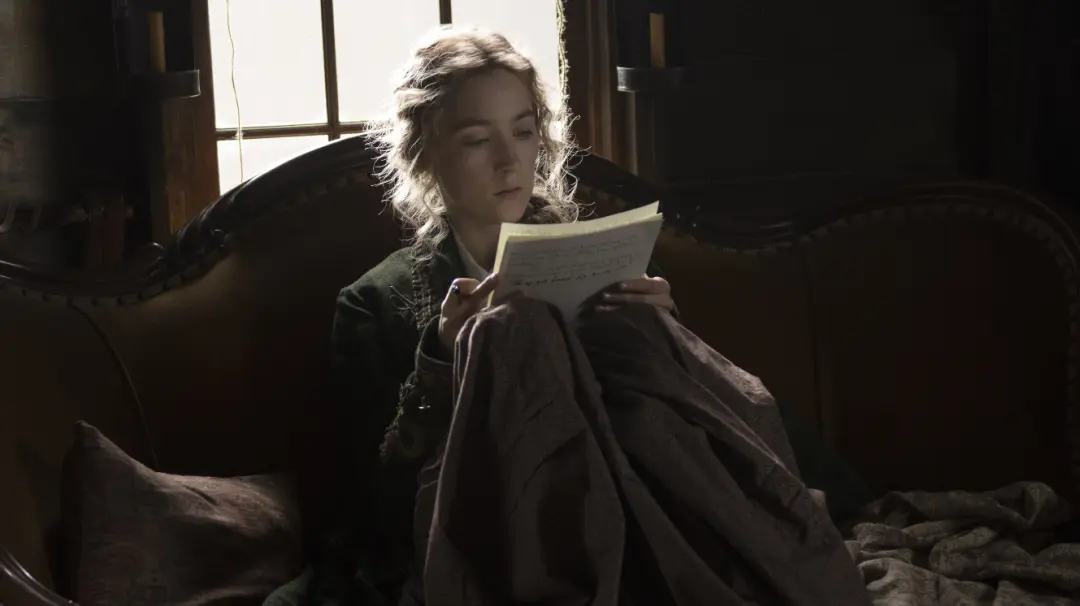
《小妇人》剧照
但小说中的社区却把独立的、有自我追求的主人公,看作是不正常的“无可救药的出格者”。当“我”被送奶工尾随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这种跟踪行为是错误的、是犯罪,而是进行一种道德化的判断,认为两个人有私情。而在这种道德化的判断里,“我”的危机被消解了,没有人发现其中的危险性,反而认为“我”是有罪的。当“我”被人下毒时,明明“我”是受害者,但由于先发的道德判断,竟被看作是“女性的堕落”。
滥用的道德评判抹除了一个人的真实的处境、真实的遭遇、真实的困难,造成与一个人真实生存状态之间的错位。
《送奶工》展现的是一个不存在善良和美好的社区如何排挤出格者的故事,小说中社区对人存在的真实境况的辨认是十分不清晰的。小说主人公“我”作为客体的他者,被社区不断用道德来指控,以至于“我”被尾随这个事情越放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罪证、一个污点。
胡桑认为,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伦理问题:我们真的觉得现代人已经自由了吗?我们真的从麦克法兰描述的古典时代来自家庭、国家和教会的三种束缚性权力中解放了吗?我们应时刻提防自身对他者的凌辱,妄加道德判断其实就是在滥用社会赋予客体的权力。只有消减掉这种权力引起的暴力,才能发现一个真正的真实存在的人,才可能去结合成为一个具有善良和美好品格的人的社区,也就是共同体。虽然小说探讨了很多晦暗的暴力的东西,但胡桑认为它并非完全没有暖色。《送奶工》中,“我”认为人和人的共存应该是去发现善良和美好,而不是厌恶和反感。这就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个认定。

《简爱》剧照
正如书中法语女教师用法语问学生天空是什么颜色时所说的:“你们面对日落时的不安,甚至是短暂的仓皇失措,都是一种鼓励。只会意味着进步,只会意味着启发。请不要认为自己背叛了自己或者毁灭了自己。”
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我”有一个几乎是笑的笑。邱华栋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许多作家都对笑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就是在某种笑声中遗忘历史和周遭的环境带来的压力,他描写的的笑趋向于某种虚妄,他以笑的方式来消解很多野蛮的造成创伤的力量,甚至用笑来对抗遗忘。而另一位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曾写过《喧嚣中的孤独》、《深夜走过的火车》、《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等等,他的书中饱含着对于自身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无奈。他的笑是小人物的笑,是一种带泪的笑。
《送奶工》的结尾,“我几乎接近笑了”,邱华栋认为,主人公是以这种方式来宣告了她自我的一段成长。她用了七个部分,来讲述自身的一段生命经验:她猝不及防的遭遇、送奶工这样一个准军事组织的男人对她的骚扰跟踪和由此产生的精神压力,以及最终送奶工的死亡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的生命经验中非常深刻的一种东西,它是挫伤也好,是打击也罢,但是最终“我”露出了一个几乎是笑的笑,获得了一种成长感。
整理撰文 | 崔健豪
编辑 | 吕婉婷 董牧孜
校对 | 李世辉
转载请超链接注明:头条资讯 » 《送奶工》:身为女性,要承受多少流言和恶意?
免责声明
: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