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小说的空间张弛有致,因为日常而更见深意。”这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对南京小说名家李樯的中短篇小说集《喧嚣日》给出的阅读推荐语。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这本《喧嚣日》之后,储福金、余一鸣等文坛名家也及时跟进了阅读快评。
储福金说,读李樯的小说,不妨从“好玩”二字着眼。“如果写作这件事情不好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如果小说本身不好玩,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是否可以判断他已经偏离了对文本属性的某种‘准确的追求’?”
余一鸣则认为,李樯的小说力量扎实,语言或密实或空净,细节处互为山水,画面一新。“短篇的好,不仅在于书面文字的张力,背后是生活的积淀,而这正是李樯的长处。”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文学批评家张学昕撰写了一篇深入的读书评论,试图揭开李樯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密码。
周末读什么好书?红星新闻《红星书评》,今日推荐李樯和他的《喧嚣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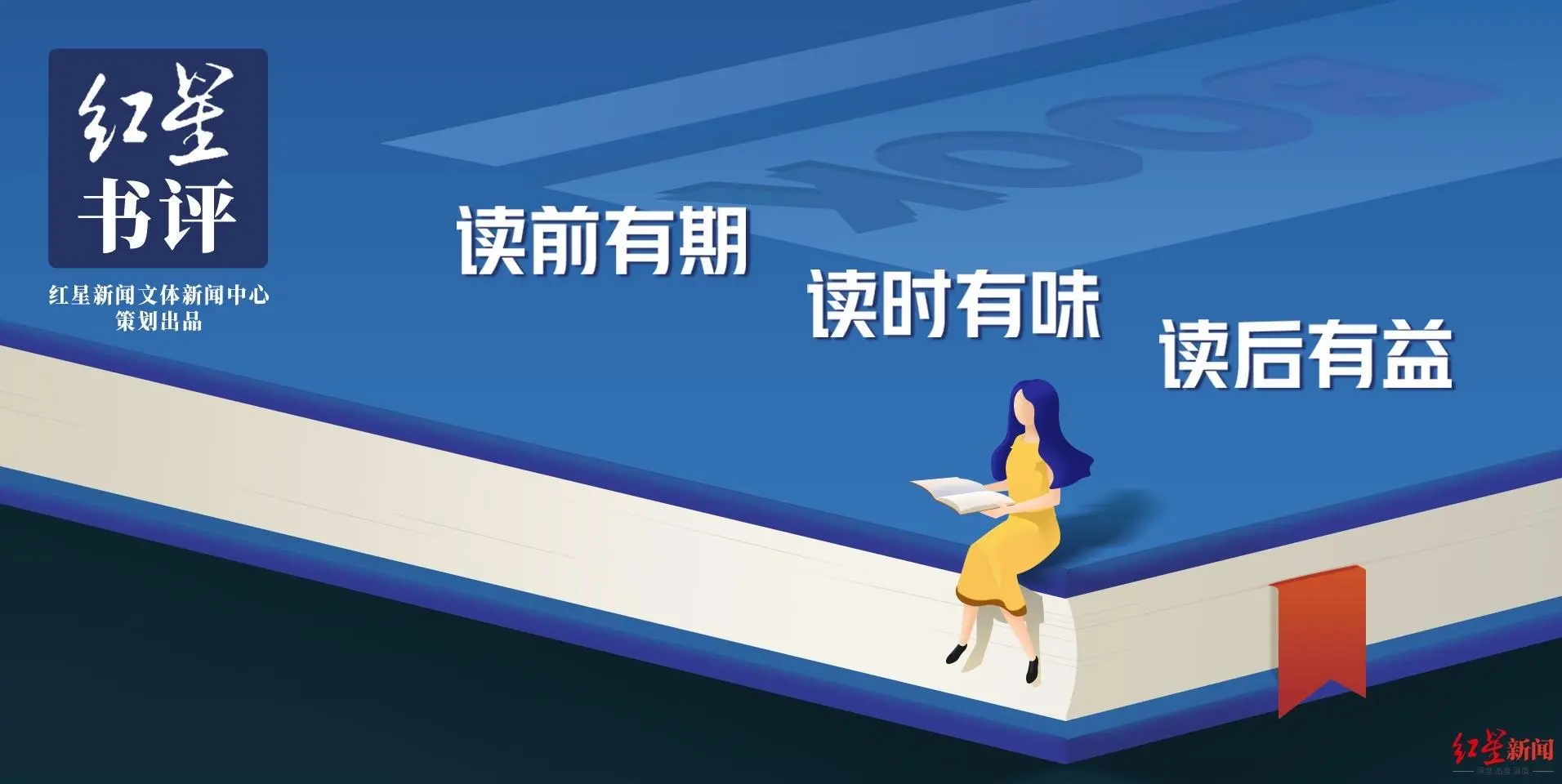
【红星书评】
触及我们生活中那些令人心动的人生世相
——李樯《喧嚣日》阅读札记
◎张学昕
短篇小说究竟能有多少叙述空间,留给细节或细部?细节是否可以构成短篇小说叙述的丰厚的主体或推进器,强有力地推动叙述的进行并带出故事、人物、意蕴,包括语言等的变化?
在一个篇幅极为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发现或开掘生活的生机和玄机,呈现可能性,都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但我在李樯的文本里,总是不断地看到触及我们时代生活中最敏感和最令人心悸的人性、精神、心理的人生世相,当然也不曾料想,他竟表现得如此细腻,无孔不入,悉力进入生活的肌理,自由而随心所欲。
我一直欣赏卡佛的小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能创造出一篇小说的张力?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引自雷蒙德·卡佛《大教堂》)
在这里,“能见度”主要是强调作家呈现生活世界的含蓄、多义性和复杂性,也就是强调文本叙述的内在张力。它不仅是考察读者的审美能力,更是测量作家的表现力的标高之一。惟有呈现出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必要的深度,才可能建立像“冰山理论”所比喻的、海平面上下那“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的文本结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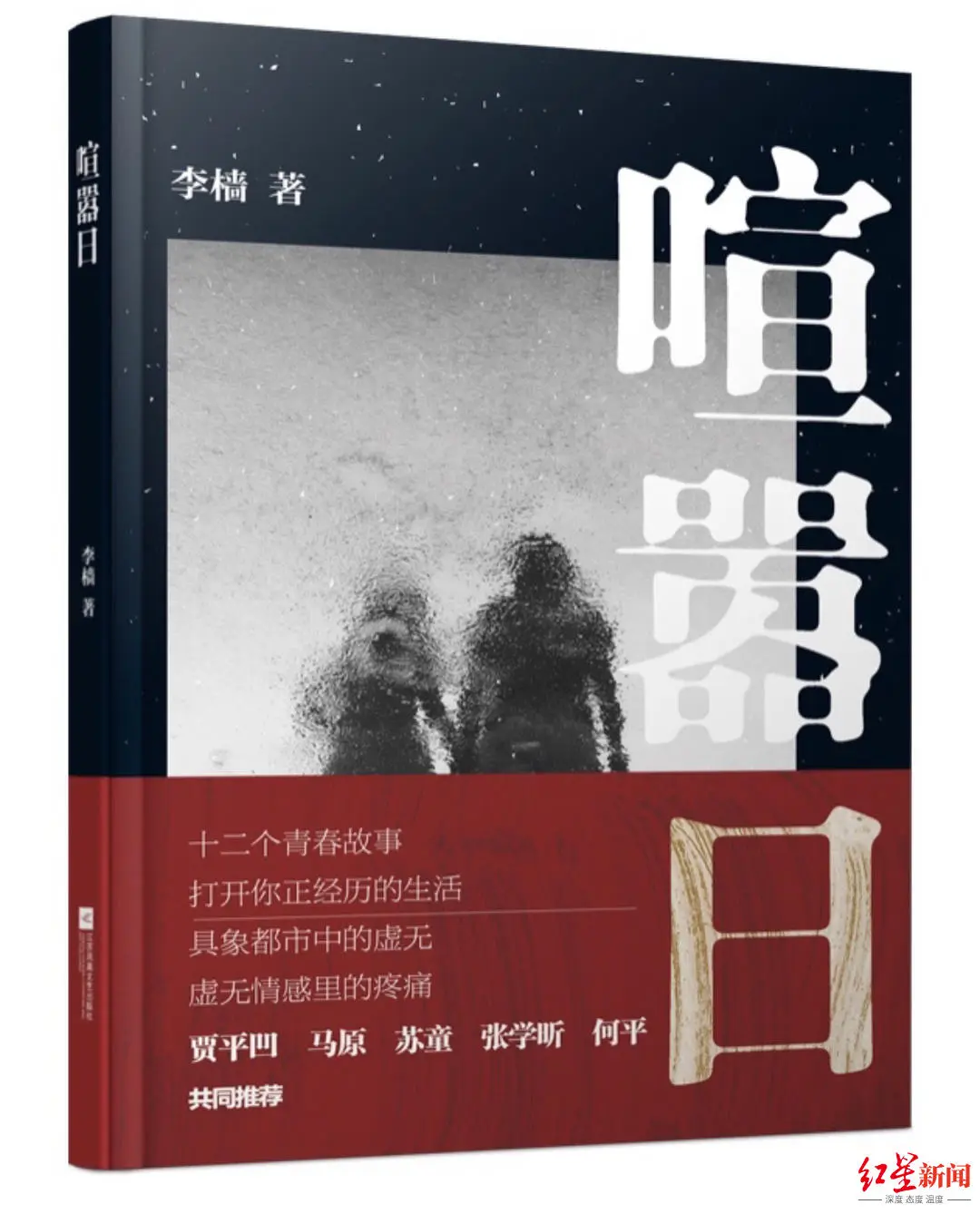
李樯始终在探究人性必须面对的精神之“难”和现实之“难”。“既然这个世界的崩溃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开始的,任何形式的外部和解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看来,人性深处的失落,如果是由于精神、信念的失守,灵魂的无所寄寓,那么,就不该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和现实。
这里,可能存在着强烈的悲观主义的基础。固然,时代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心理、精神、人性带来了负累、沉重与惶惑,但是,若是从另一种寻求灵魂安妥的向度看,它们也为人们的内心担负起太多本不属于它们的“罪名”和责任。所以,人的幸福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必须要经常地扪心自问。或许,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至此,我们又要重新追问“我是谁?”的终极问题,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寻找生活和存在的精神“上游”,都要解决“为什么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
而李樯的《星期五晚上干什么》呈现了青春期稍纵即逝之后的孤独,心理空间的日渐逼仄引发出精神的虚空。一代人的焦灼,依然不断萌生出现实碾压下灵魂无处安放的错觉。周末到来的时候,现代生活情境下,究竟应该有一种怎样的休憩,或一种短暂的心境的调整?故事里的“他”在以往的惯性和“套路”里,与同居女友约会不成之后,幻觉和空虚蜂拥而至。芜杂混乱的生活情趣,无法捡拾起曾有的旧梦。“那个冬天的晚上,他没感觉到过孤独。那时他还有一点爱情,有一点幻想。五年后的冬天,他已变得一无所有,爱情早已逝去,幻想已被庸俗的生活挤兑得跌入深渊。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像冬夜的风一样的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
当“他”约到昔日的女友的时候,共同的无奈和重新面对困惑,都无法获得丝毫情感和心理的补充与宽慰,一丝回忆立刻引发两者的无限感慨:爱情和婚姻为什么竟然可以肆意地随风飘散?也许,生活中哪怕一点点错位,都可能在脆弱的心灵上制造偌大的毁损。也许我们会替她们重新思考,决定他们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是信仰,而不是摆脱当下的孤独。
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们在一起好好的,从没拌过嘴,你说分手就分手,好像一点也不伤心,一点也不眷恋。
有什么好伤心、眷恋的。一天早上醒来,冥冥中好像有个声音对我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于是就决定和你分手了。我很信命的,我们的一切,在前生就都已经决定好了。
如果一个人在周末感到无聊至极,极为尴尬,特别是“聆听”前女友如此坦然的、充满宿命论的表白,我们对生活应该做出怎样的判断和理解?消极的、向下的、低调的生命情境和氛围,滋生出无可掩饰的苍凉。而他们讲起这样的境遇时,竟是如此轻松,不以为然。李樯小说有意无意间,揭示出生活中隐藏的人性的幽暗,洞悉出人生关键期可能面临的危险地带。
作家所要呈现的人性和生活世界,难免具有作家“个人性”的烙印,依然脱不掉自我、自信、“自以为是”的任性的干系。但这种“个人性”,应该是作家自我“隐身”“忘我”的异质性经验之体现,因为我们无法确认个人性的经验,就是人类经验中的具有超越性的美学经验。
纵观李樯这些中短篇小说,虽然我们无法回避其中作家个性倾向的“隐形”存在,但李樯的小说有着奇异的宽阔,其中蕴借着人性和生活的精微与丰富。因为一己的经验,只有在嵌入另一种个性、人性,滋生出“忘我”性的生活重构时,才能够进入超越自我的层面。
说实在的,李樯的小说在叙述层面上并不细密、细腻,但它依靠整体性的合力和个体的冲击力,获得对生活和人性的穿透力。我感觉,《喧嚣日》结尾的那段叙述,似乎能够隐喻出李樯小说创作中人物、故事、记忆、时间和人性诸多层面在哲性思辨基础上的精神品质:
尖叫犹如夜空的流星,照亮了谢东民脑海深处的许多幕情节。这一幕幕情节就是一枚枚感光底片,谢东民的脑海则是一间暗房。那些底片堆砌在一起,在东民的脑海里就那么一闪,很难让他理出一个事件上的或情节上的顺序。他只能凭借记忆,下意识的凭空抓一把,将一些难以忘怀的东西简单迅速的回忆一番。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类似底片的回忆中,东民看到的是白色的毛发、白色的眼球,黢黑的面孔。原初的事实一旦跌入回忆,便会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着一个对立面。
特别是最后一句“原初的事实一旦跌入回忆,便会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着一个对立面”,这像是对李樯小说写作所作的一种宿命般的描述和判断。“原初的事实”,成为他中、短篇小说的整体体貌里的飘忽不定的因子,虽无法聚敛,但可以成为叙事中结实的硬核。
我感觉,李樯是一个怀疑论者,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境界不俗的小说家,他敢于敏锐地将精神体验的极端意绪表现出来,也没有太多凡俗的顾忌,我坚信那些故事里一定有他自己曾经沉浸其间的青春“底片”。虽然,文本呈现出的情趣、意趣和审视现实的“精准度”,不免会时有偏差,但李樯的格局绝不偏狭,他有自己的想象方式,也有叙述耐心、耐力,他不会遮蔽生活、现实和人性底部的隐秘,而能够将“跌入回忆”的往事过滤、沉思并“打捞”上来。(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文学批评家)

李樯
【作家简介】
李樯,江苏徐州人,诗人、小说家、影视编剧,《青春》杂志总编。已发表有小说近百万字、诗歌两百余首。出版有长篇小说三部,小说集《喧嚣日》,诗集《挑灯夜行》,与鲁羊英文小说合集一部。曾获南京文学艺术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编辑 乔雪阳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转载请超链接注明:头条资讯 » 红星书评|李樯《喧嚣日》:揭示出生活中隐藏的人性的幽暗
免责声明
: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