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星花园》、《恶作剧之吻》、《一起来看流星雨》、再到近几年的《亲爱的,热爱的》、《下一站幸福》,偶像剧总是因为过于模式化和人物的脸谱化被诟病为“玛丽苏甜剧”。尽管如此,不断重复的“甜甜的恋爱”的偶像剧总能获得稳定的收视率。尽管观众承认偶像剧炮制的恋爱故事并不现实,但这不妨碍他们投射自己的情感,代入主人公的同时产生愉悦感和认同感。
与现实生活中被观众痛斥的“渣男”不同,男主人公总是把女主人公视为唯一牵挂的对象,让她得到情感的濡养和尊重。从这个角度来说,偶像言情剧也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情感补偿,满足了观众对忠贞爱情的渴望。

《亲爱的,热爱的》剧照。
今日的言情偶像剧也能在浪漫小说提供的理想爱情模式中寻到踪迹。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主妇是浪漫小说的忠实粉丝,无论家务有多繁忙,她们都会抽出时间阅读,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主妇阅读浪漫小说的社会背景、心理需求以及产生的影响也能为女性对浪漫爱情的想象提供一种解读背景。
这些热衷于浪漫小说的主妇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浪漫小说炮制的爱情故事是否会在满足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浪漫想象的同时加重了性别刻板印象,维护父权统治?如果说,主妇是出于不满才阅读,那么浪漫小说又是如何利用爱情故事消解这种反抗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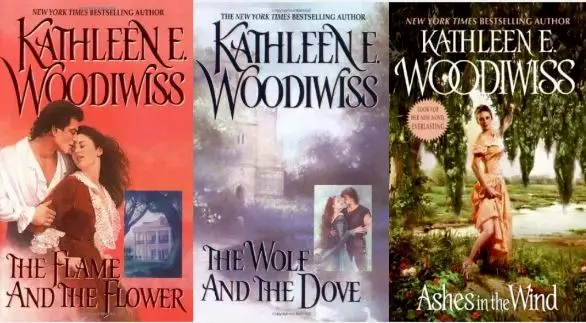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伍德威斯是上世纪70年代开创浪漫小说的先驱人物。伍德威斯的作品至今仍高居各大书评网站历史言情小说榜单的前列。
和现在的言情偶像剧一样,浪漫小说作为一种补偿性文学为主妇提供了一场理想爱情的浪漫之旅。主妇们在小说描绘的异域风光中,体验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在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关怀备至、忠贞不渝的爱情中得到情感的濡养,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伴侣身上无法实现的渴望。主妇能够在这样的阅读中释放、缓解自己的不满,并尝试寻找解决之道。她们试图相信在理想的爱情模式中,女性的才智和独立会得到欣赏,她面临的被强奸和凌辱的威胁可以被白马王子拯救,而自己的情欲也可以在伴侣身上得到释放,她们能够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同时保留自身的主体性,而非迷失在日常生活制造的牢笼中,一味地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但是自己的情感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和关注。
然而当浪漫小说的叙事策略试图以“理想的爱情”为核心解决主妇的困难,却避而不谈让女性备受限制的社会文化结构时,原本具有反抗效果的爱情故事就会逐步消解这种反抗,浪漫小说就只能作为暂时逃避现实的情感补偿和缓冲地带,大多数主妇放下书本后仍旧回到日常生活,再次被失落感击中。
撰文|汤明明
浪漫小说:逃离日常生活和“贤妻良母”身份的乌托
邦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中对热爱浪漫小说的主妇进行调查,试图探究浪漫小说吸引主妇的原因以及对她们产生的影响。在和史密斯顿热爱浪漫小说的主妇进行长期交谈后发现,主妇正是出于对父权统治引发的情感后果的不满才进行阅读。那些备受主妇喜爱的理想的浪漫小说也强调了女性不愿意被男性掌控的意愿,以及对女性的才智和独立的赞赏。主妇阅读浪漫小说的渴望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对平等、尊重的亲密关系的渴望和维护自身主体性的追求。
长期以来,主妇阅读“浪漫小说”的爱好总会遭到贬低和反对。在主流文化中,它被视为轻浮、暧昧、露骨、色情的爱好,自诩品味高雅的男性(包括图书出版商)总是嘲讽阅读浪漫小说的主妇,将浪漫小说视作“女性鸦片”。在家庭中,她们有时也需要偷偷摸摸地阅读,因为这种行为总会引发丈夫和孩子的不满,虽然丈夫的不满与妻子所看的书籍类型并无多少关联,他们更加抗拒的是妻子的沉浸式阅读会减少在自己身上投入的精力。主妇也会因为自己的爱好产生愧疚和自责的情绪,反思自己是否在小说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即使没有证据表明她们会因此疏于照顾家人,或是效仿书中的女性在昂贵的衣饰上耗费大量的财力。

《阅读浪漫小说》,[美] 珍妮斯·A ·拉德威 著,胡淑陈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7月。
尽管阅读过程总会遭遇阻碍,主妇也不愿意放弃阅读浪漫小说的爱好。她们试图为自己的阅读权利辩护,声称这种兴趣爱好和男性喜爱的电视节目无异,都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不过主妇并没有单纯地将浪漫小说视为纯粹消磨时间的方式,她们不仅有意识地将它安排进日常生活中,还试图将自己的阅读行为与美国中产阶级相信知识与成功和地位紧密相连的价值观相联系,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合理化自己的阅读需求。
拉德威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小说描绘的浪漫爱情,史密斯顿的主妇对小说中描绘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也相当感兴趣,十分注重浪漫小说的教化功能,认为自己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城市风貌,开拓视野和见识。当主妇将自己在小说中学到的诸如烹饪手法、当地的风俗习惯、交通方式以及地理风貌(越晦涩越生僻越好)告诉自己的丈夫时,他们就不再生硬反对妻子的阅读爱好,甚至转身将这些知识转述给他人。主妇在讲述自己从小说里学到的知识时也获得了“暂时的权威”,可以证明自己并非是文化刻板印象的实列——“头脑简单的家庭主妇除了喂养孩子、熨烫些衬衫和看一下午的肥皂剧外一无所能。”
但主妇绝非只因为浪漫小说呈现出的百科全书的特征醉心不已。史密斯顿的女性普遍认为阅读浪漫小说是逃离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拉德威指出浪漫小说“不仅能让人从日常问题及责任所制造的紧张中脱身而出,而且还创造出一个女性可完全独自享有并专注于其个人需求、渴望和愉悦的时间或空间。这同时也是一种通往或逃到异域,或者说不同时空的方式。”主妇可以通过阅读浪漫小说创造“私人空间”,让自己短暂地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向他人宣告这一段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妇的阅读行为本身就可以算作是一种“独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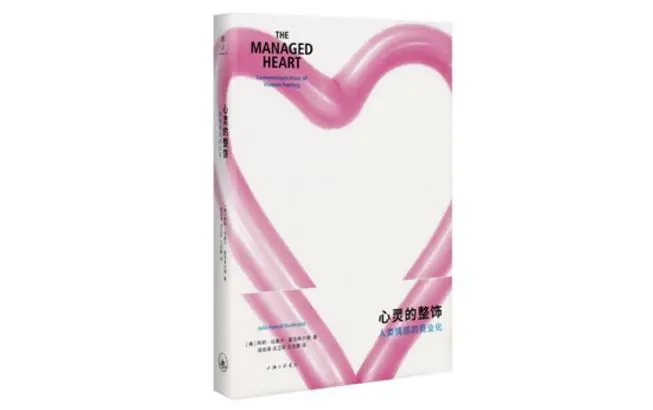
《心灵的整饰》,[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成伯清 淡卫军 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
拉德威发现主妇渴望通过小说逃离日常生活,暂时摆脱“贤妻良母”的身份与主妇缺乏情感支持相关。属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总被要求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却鲜有人意识到她们自己的情感需求,以及这些需求被不断忽视和难以满足时的孤独和痛苦。
美国情感社会学学者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也佐证了这一观点。霍克希尔德指出女性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她们被要求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合作性”,以便更好地照管孩子和丈夫的饮食起居以及心理层面的需求,源源不断地提供爱的服务。这时阅读浪漫小说就成了她们疲惫时的一个缓冲地带。拉德威认为,史密斯顿钟情浪漫小说的女性与桃乐茜·霍布森研究的靠收音机和肥皂剧排遣孤寂感的主妇同具有相似之处,“用她们的书籍在自己与家人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从而宣布她们暂时闭关,不准那些想要向她们索求情感支持和物质照料的人踏入半步。”

美国浪漫小说先驱人物凯瑟琳·伍德威斯(Kathleen E. Woodiwiss,1939-2007)。
补偿性文学和幻想性解决策略
那么为什么相比侦探小说、西部小说等通俗畅销读物,主妇更愿意选择浪漫小说作为自己逃离日常生活的方式呢?拉德威认为浪漫小说也往往会成为“补偿性文学”(compenstory literature),弥补主妇难以在男性伴侣上实现的需求和渴望,从女性的角度构建理想的异性恋关系,并尝试提供一种解决策略。
拉德威在采访中发现,备受读者喜爱的浪漫小说的男主人公总是在富有男子气概的同时温柔体贴,懂得欣赏女主人公身上的品质,始终将女主人公当作唯一关注和牵挂的对象。读者也极易在这样的文本中满足对爱情/婚姻的浪漫想象。虽然主妇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并不现实,但她们又乐于在女主人公身上寻找相似性,在产生认同和代入感的同时得到“被呵护以及情感得到濡养”的感觉。此外相比那些揭露了现实残酷性的小说,史密斯顿的女性更喜爱那些皆大欢喜的结局。
虽然主妇们认为“完美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她们不喜欢作者“长篇累牍地描写残障或缺陷”因为前者会让主妇勾起痛苦的回忆或对生活失去信心(比如曾经被抛弃的经历或贫苦的生活l),而男女主人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般的结局能向主妇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安抚心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妇就会沉溺在浪漫小说编织的童话世界中,盲目地产生认同。有意思的是,她们的自我意识甚至会被一些糟糕的“浪漫小说”启蒙。史密斯顿的主妇会将自己和那些软弱、轻信的女主人公进行对照,反思自己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弊病。主妇也并非全盘接受所有类型的浪漫小说,有意思的是,理想的浪漫小说除了描写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也会凸显女主人公的“独立”和“才智”。在拉德威“一个形象动人的女主公应该具备什么特点”的调查问卷中,主妇将“才学”、“幽默”和“独立”视为最为重要的品质。男主人公对聪明、独立的女主人公的青睐也让她们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成为母亲和妻子的同时保留自身主体性。
这与人们通常对浪漫小说中女主人公软弱、无助的印象产生了出入。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顿德的主妇在对女主人公的品质和行为作出判断前,默认了男性是资源和权利的掌控者的事实,虽然她们反感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男性轻视以及那些将家庭主妇视为愚蠢和无足轻重的“女性解放者”,但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可以和男性一样具有同等的能力。因此那些女权主义看起来依旧是依附于男性,不够彻底“独立”的女主人公却依旧被主妇认为是相当有胆量的。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并未意识到压迫女性的深层原因,仍然像女主人公一样将爱情视作人生要义,但浪漫小说也或多或少吸取了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积极成果——不管浪漫小说是否真的能帮主妇实现这一点,但至少她们希望“独立和稳固的个人身份并不会因为受到男性家长式的作风的呵护和保护就受到伤害。”

图为《致命女人》剧照(图片来源:豆瓣)。《致命女人》中以1960年代为背景的夫妻在餐桌上的对话可以从侧面证明,在传统的中产阶级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属于家庭,她所需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丈夫,而内心需求却一直被忽视。
浪漫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的情欲正名,提供了“一种情感呵护以及情欲期待和兴奋的替代性体验。”虽然主妇们在被问及小说中的性爱描写时总是流露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声称出版商印在书上的“丰乳和裸体”会让她们难堪,甚至想把书藏起来。但如果性爱是发生在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主人公之间,男主人公体现出温柔和玉树临风的特质,女主人公感受到了温柔和关爱,主妇就会欣然接受,也不排斥大段露骨的情爱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小说的变革也受到了女权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浪漫小说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情欲的描写让一些人感到不安,认为女权主义毁掉了浪漫小说。另一方面有的作者甚至自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的理念和女权主义者有相通之处。拉德威解释道:“我们也无法断言说,那些努力将女权主义要求纳入这一文类的作者是因为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形式的内在矛盾性,还是受迫于文化大环境向前发展带来的压力。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浪漫小说的变革本身是争取界定和掌控女性情欲权利的大潮之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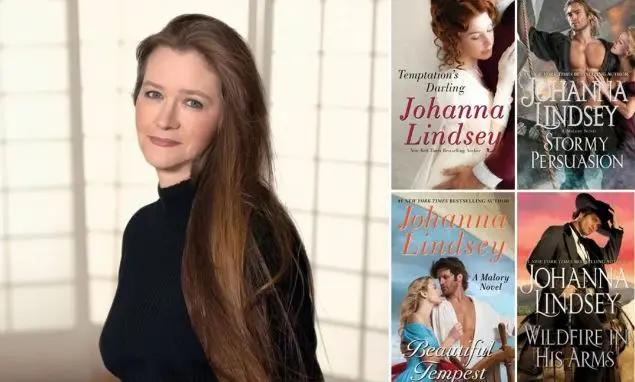
去年逝世的美国浪漫小说作家乔安娜·林赛(Johanna Lindsey,1952-2019)。她的所有作品都能跻身《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其中不少更是居于榜首。
浪漫小说的局限性:反抗随阅读停止
值得追问的是,如果主妇是出于在社会和家庭中位置的不满进行阅读,那么这种由父权统治引发的情感后果是否会在阅读完成后消失?浪漫小说所炮制的爱情故事是否会消解主妇原本可能产生的反抗?
虽然女性在阅读浪漫小说时不仅获得了浪漫想象和情绪补偿,也能找到应对自身的情感需求和主体性与传统异性恋关系的矛盾的解决策略,但是这些策略都以异性恋的爱情为核心,浪漫小说原有的反抗色彩会逐渐失效。虽然理想的浪漫小说中,女主人公一出场就具有中性气质、对陈规陋习报以批判的态度。但这并非是有意破除性别刻板印象,挑战男性的权威。拉德威发现这些女主人公在出场时的社会身份往往遭到破坏,乔扮男装或对异性的敌对态度代表了主人公“破碎的身份”,随着恋情的推进,女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美丽大方、充满情欲渴望的女人,这预示着女主人公实现自我的方式依旧是找到“真爱”。故事的结尾也仍旧屈从了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将婚姻视为生活的理想形态,把父权制婚姻描述为实现成熟女性主体性的最终道路。
另一方面,浪漫小说也试图呈现男主人公的“蜕变”,却无法从根本无力解决“‘如何让男性变得温柔体贴’这一棘手的问题”。男主人公在感情方面却往往风流成性、冷酷无情,呈现出“爱情缺失”的特征。然而他的滥交和冷漠并非是致命的缺陷,相反是没有遇到真正的爱情时的体现——这也成了女主人公顺利出场的理由。读者可以假想,正是因为女主人公的感化,他才从一个看似冷漠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变成一个温暖贴心,情话绵绵的爱人。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今日流行的言情小说和偶像剧中仍然清晰可见,表面不通人情世故的“霸道总裁”和“浪子回头”的叙事依旧可以填充读者对浪漫爱情的想象。但这样的故事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女主人公和读者都相信男主人公发生了蜕变,但这并不来自于他的主动改正,而是女主人公在经历过重重误解之后,发掘出了他本身就具有的,隐藏的温柔又善解人意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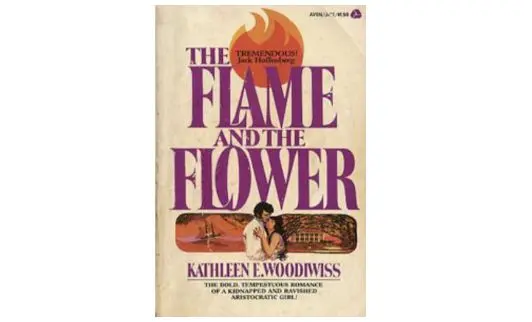
浪漫小说作者凯瑟琳·伍德威斯于1972年由埃文书屋发行的《火与花》。这本小说在拉德威的女性最喜爱浪漫小说调查问卷中位于第一。
此外浪漫小说虽然反映了女性面临男性的暴力和被强奸的威胁,但是浪漫小说给出的解决策略并非是反击“强奸文化”而是继续依靠爱情化解。小说中,男二号经常扮演“反叛角色”,让女主人公陷入被凌辱和强暴的威胁,不过浪漫小说不会让女主人公在这种陷阱中停留太久,她必定会被男主人公营救。这种“英雄救美”的解决策略使女性相信如果她找到了“白马王子”,就可以永久消除威胁,亲密关系中广泛存在的暴力和女性易沦为性玩物的事实就被大团圆的爱情故事巧妙掩盖了。
虽然浪漫小说的确对主妇产生了积极影响,她们开始拒绝被丈夫支使得团团转,在阅读被丈夫反对时,为了获得购书资金出门工作,有的女性读者甚至开始自己创作浪漫小说,将缝纫室变成书房,挑战了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但是浪漫小说的欺骗性在于用“理想的浪漫爱情”解决女性的困境,向她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承诺。这就导致了原本涌现的反抗色彩被逐步安抚和削弱,原本作为抗议阵地、控诉父权制引发的情感后果的浪漫小说却不再质疑父权制控制女性的制度化基础。主妇的“反抗之旅”也随着阅读之旅结束,如拉德威所说“我们无法创造出一个不必依靠阅读获得创造性愉悦的世界。”
撰文 | 汤明明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王心
封面图片来自电影《爱乐之城》剧照。
转载请超链接注明:头条资讯 » 浪漫小说是“女性鸦片”吗?
免责声明
: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