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大学问家花拉子米在巴格达把他那本教人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书用裹尸布包好,题献给有波斯血统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这标志着代数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如果我们认定那一年是公元820年,距今(2020年)正好一千二百年了。
这书的书名阿拉伯文为Al-kitāb al-ğabr waal-muqābala(The Book on Calculation by Completion and Balancing),书名中al-ğabr(或者al-Jabr)的拉丁拼法就是Algebra(代数)。《堂吉诃德》中曾经出现过algebra一词,指的是正骨术,这和它的阿拉伯文原意差不多。花拉子米还有一部伟大的著作Al-kitab al-ḥisāb al-hindī[《印度算术书》(The Book of Indian Computation)],这本书介绍了印度十进制记数法,以及基于十进制的加减乘除和求根算法。因为正文开头第一句是“花拉子米说”,于是在被翻译成拉丁文后,书名就成了《花拉子米的印度计算法》,或简称《花拉子米》。“花拉子米”(al-Khwarizmi)的拉丁拼法是Algorizmi,这个词再译成英文就成了Algorithm,也就是现在计算机科学的核心概念:算法。当然算法的严格定义还要再等一千一百多年,是图灵1936年在那篇惊世之作中描述了被称为“图灵机”的装置,人类从此才对原来只有直觉印象的算法有了彻底深刻的理解。花拉子米的算术书在欧洲传开后,人们习惯称书中的记数法为“阿拉伯数字”,其实那是“印度数字”。埃及裔法国科学史家拉希德(Roshdi Rashed)说花拉子米的代数本身就有算法的性质。
博学的大数学家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史》副标题就是“从花拉子米到爱米·诺特”(A History of Algebra: From al-Khwarizmi to Emmy Noether,1985),这书明确了花拉子米是代数之父。爱米·诺特是杰出的女数学家、哥廷根学派的代数大家、范德瓦尔登的老师。历史写到老师为止,恰如其分。范德瓦尔登本人是德国哥廷根学派和法国布尔巴基学派之间的桥梁,他从哥廷根走后,德国数学没落,法国数学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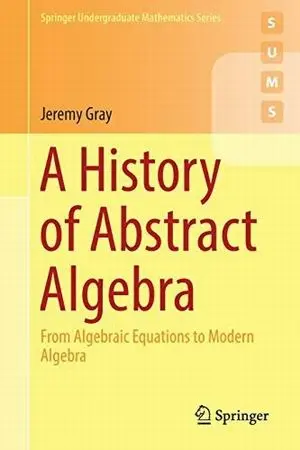
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史》
一般的数学通史对花拉子米两本书的成书时间并没有考证,只是笼统地说是公元813年到833年之间。道理很简单,那恰是赞助花拉子米的哈里发马蒙在位的时间。最早把花拉子米《代数学》翻译成英文的是美国数学史开拓者卡宾斯基(Louis Charles Karpinski),他曾经说过花拉子米创作的高峰期是公元825年左右,于是晚辈史家也受此影响,把825年定为成书年。这也影响了科学史的研究者,如科学史家哈弗(Toby Huff)的那本研究比较科学史的大著《早期现代科学的兴起》(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也随大流说825年。
花拉子米两本书的成书时间是不同的,《算法书》中提到了《代数书》,证明《代数书》成书应该更早。当代对阿拉伯语数学史和科学史最有研究的就是埃及科学史家拉希德,他于2006年重新翻译了花拉子米的代数书,先译成法文,再于2009译成英文。书前有拉希德的九十页长文,详细考证花拉子米的生平和该书的版本源流,他认定这书应该在820年写成。近年的文献遂形成“820年”的共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会资助翻译的《算法与代数》是花拉子米两本书的合集,译者也随“820年”之说。中国数学家兼诗人蔡天新2017年出版的《数学简史》中也如是说。
一般认为花拉子米公元780年左右生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希瓦城(Khive),公元850年左右逝于巴格达。波斯历史学家塔巴里(Al-Ṭabarī,不是更早的翻译家塔巴里)生于公元839年,很接近花拉子米的年代,他有个说法:花拉子米是在巴格达附近出生的,只不过祖上来自波斯的呼罗珊地区(Khurasan,现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交界的一片地区),花拉子米有个诨号al-Quṭrubbaliyy,而这个诨号蕴意他来自Qutrubbul。这是个离巴格达不远的地方,在第比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盛产葡萄。但此说一般被认为不靠谱。至于他的宗教也有几种说法,一种是他生来就是穆斯林,另一种是他小时信拜火教,长大后改宗。花拉子米受教育的地点应该是在中亚古城木鹿(Merv,或译默夫)。在阿巴斯王朝期间,木鹿城是呼罗珊的都城。
公元529年,断断续续存在了九百多年的柏拉图学院和稍晚的亚历山大城的学校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关闭,部分学者逃到波斯的贡德沙普尔(Gundishahpur,或拼为Jundishahpur),那儿当时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学术中心。萨珊君王霍斯劳一世(公元531年-579年在位)崇尚文化和学术,在他的地盘,有希腊人、叙利亚人、基督徒、景教徒、犹太人,大家和睦相处。他还引进了印度文学和学术。

查士丁尼大帝
阿拉伯征服者继承了萨珊王朝对文化的宽容。公元750年,萨法赫(Saffah)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阿巴斯王朝并扩张迅速,公元751年,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Abu Muslim)的部将齐亚德(Ziyad ibn Slih)在怛罗斯击败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流行的传说是中国俘虏中有造纸匠,于是造纸术传到中亚,工匠们在撒马尔罕建立了造纸厂,后巴格达成为造纸中心。芝加哥大学汉学家钱存训曾为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撰写《纸与印刷》一卷,他指出中亚在怛罗斯之役前就有造纸术。活跃于十四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提到造纸术时也没提中国。无论如何,纸促进了阿拉伯文明的繁荣。
伊斯兰世界被阿巴斯王朝一分为二,东边是强势的阿巴斯王朝,西边则是后来逃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倭马亚王子建立的后倭马亚王朝。萨法赫的弟弟、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bu Jafar Al-Mansur)不喜首都大马士革的传统部落氛围,而更心仪波斯发达的文化和官僚体制,一心想迁都。在占星家的指导下,新都选址在离巴比伦古城不远的巴格达。公元766年,阿巴斯王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了新城巴格达。
曼苏尔统治时,开始翻译希腊著作。到了第七任哈里发马蒙,阿拉伯翻译运动进入高潮。此时的阿拉伯世界是世界文明的顶峰。马蒙的母亲是波斯奴隶而成的妾,他姥爷其实是呼拉珊地区的起义领袖。前任哈里发是马蒙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明,是纯种的阿拉伯人。马蒙击败了阿明。英籍伊朗裔物理学家兼科学史家哈利利(Jim Al-Khalili)认为,马蒙代表更加开放多元的波斯文化,而阿明则代表传统的阿拉伯文化。阿威罗伊是阿拉伯世界最后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他曾无奈地宣称:逻辑和信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最好各行其事。哈利利认为马蒙的时代是逻辑和理性的时代。
马蒙继任哈里发之后的第六年(公元819年)才进入巴格达,没多久就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中见到了亚里士多德,他问亚里士多德:“何谓善?”答曰:“一切符合理智的东西。”再问:“还有呢?”再答:“人民认为善的东西。”再问:“还有呢?”再答:“没了。”这有点像五四运动的口号,赛先生(科学)第一,德先生(民主)第二,没有其他。这段故事出自公元十世纪的阿拉伯书商兼文献学家纳迪姆(Ibnal-Nadim)所著《书目大全》(Al-Fihrist)。纳迪姆把他所知道的书按作者词条编撰成册,这书是阿拉伯学问的重要参考书,纳迪姆自称这是“所有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所有著作的索引”。关于花拉子米的著作和生平,这书也是原始出处之一。在花拉子米的词条下只列出了他的天文学著述,却误把他的两本最重要的著作《代数书》和《算法书》归到另一个词条al-Yahudi下面,估计是抄写者犯的错,因为al-Yahudi词条恰好在花拉子米词条之后。从这书其他词条对花拉子米词条的引用来看,确实是抄写错误。这书直到1969年才由道奇(Bayard Dodge)译成英文,分上下两册,共一千两百多页。道奇曾接任他岳父担任过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长。书中涉及数学和科学的内容,翻译似有改善的空间。上面提到的马蒙的亚里士多德之梦的译文来自哈利利,而道奇的译文则意思多有不同。
有人说是亚里士多德之梦激发了马蒙对知识的兴趣,于是他资助翻译运动,并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宫。智慧宫中有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是继被焚毁了的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和学校之后最大的学术机构。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亚历山大城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都被运到巴格达,收藏在智慧宫内。这些年很流行大历史。写大历史的人往往忽略或者弄错很多细节,历史没有了这些细节远离真实,也缺少趣味。泛文化史或思想史的人要比科学史的人更不严谨,而科学史的人要比数学史的人更不严谨,做数学通史的人自然也会忽略代数史的细节。就像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难的,数学史也是所有知识史的分支中最难的。历史做得越大,越弄不清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例如,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思想史》(Ideas: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把马蒙建立智慧宫的时间定为公元833年,但这恰是马蒙死的那一年,马蒙死时,智慧宫已经名满阿拉伯世界了。作者都懒得核实马蒙的生卒日期。研究历史有点像丈量海岸线,量出来的结果取决于尺子的长度。
1258年2月13日,成吉思汗的孙子托雷的儿子旭烈兀(Hulagu)攻入辉煌了五百年的巴格达,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烧杀抢掠。智慧宫内超过一百万卷藏书的大部分被扔到底格里斯河中,据说书上的墨将河水染黑。数学家图西(Nasir al-Din al-Tusi)在城破之前把智慧宫收藏的一小部分抢运到马拉盖(Maragheh,位于伊朗的阿塞拜疆省)。图西后来得到旭烈兀的信任和资助,又在马拉盖建立了著名的马拉盖天文台,最后官至首相,死在巴格达。图西是最早提出地动说的人之一,还修订过《几何原本》。蒙古人见过世面,征服中国后知道当地没有科学,于是分别从马拉盖和撒马尔罕邀请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到广州和北京,旨在修建天文台并修订历法。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间太短,阿拉伯的知识在中国没有传开。再后来,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和大臣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但影响不大。中国人再接触科学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
现在已找不到智慧宫的遗迹。摩洛哥旅行家白图泰十四世纪到过巴格达,他看到的是庞大但衰败的城市。现在对智慧宫的想象都来自古人的描述。也许它不只是单一建筑,甚至不是单一园区,而是巴格达城里所有知识机构的统称。耶鲁的阿拉伯专家古塔斯(Dimitri Gutas)在《希腊思想,阿拉伯文化》(Greek Thought,Arabic Culture)一书中提醒人们,不要把智慧宫夸大或神话。“智慧宫”的阿拉伯文Baytal-Hikma中Bayt是房子的意思,而hikma则是“智慧”或者“推理”的意思,更多偏科学。所谓“智慧宫”也可译为“科学之家”(House of Science)。十一世纪埃及建立的Daral-Hikma更接近“智慧宫”(Hall of Wisdom),dar要比bayt更加宏伟。似乎阿拉伯翻译运动并没有翻译多少希腊的文学作品。
近年出版的两本名为《智慧宫》(House of Wisdom)的书都很好看。一本的作者就是物理学家哈利利,另一本的作者是记者出身的莱昂斯(Jonathan Lyons)。哈利利的书在英国的平装版又名《寻路者》(Pathfinders: The Golden Age of Arabic Science),内容和美国版《智慧宫》大致相同,中文按英版译出。关于花拉子米,哈利利更多讲《代数书》;而莱昂斯更多讲《算法书》,以及它在欧洲的传播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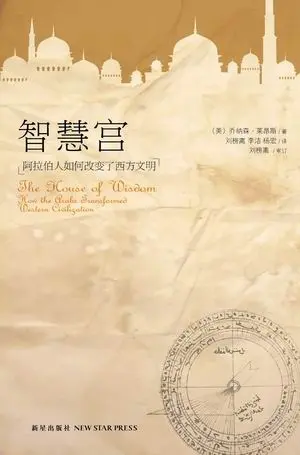
莱昂斯所著《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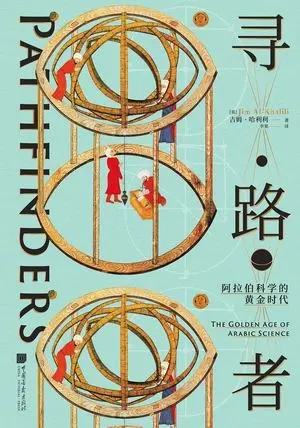
哈利利所著《寻路者: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
关于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学术,应该叫阿拉伯学术,还是叫伊斯兰学术,一直有争议。阿拉伯人占领了叙利亚和波斯之后,当地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在帝国早期,阿拉伯人相当开明,犹太人、波斯人、景教徒都不必改宗。按照哈利利的说法,凡是以阿拉伯语写作的都该算阿拉伯学术或者阿拉伯语的学术。当时的阿拉伯人掌握着统治的语言,这语言却没有承载内容,智慧宫的一位阿拉伯翻译家说:“我们掌握语言词汇,他们(波斯人)却拥有思想。”波斯人也不谦虚,他们甚至认为希腊的学问都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从波斯偷走的,然后烧了波斯的原著。
智慧宫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是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Abu Zayd Hunayn ibn Ishaqal-Ibadi,808-873)。他是景教徒,专业是医药,出生在希拉(Al-Hirah),即库法城,他会叙利亚语和波斯语,后在巴士拉城学了阿拉伯语,在亚历山大城学了希腊语。马蒙为了搜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派了一队学者到拜占庭求书,伊斯哈格应该位列其中。伊斯哈格翻译了大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一般先把希腊语翻译为叙利亚语,再由别人(很多情况下是他儿子)从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他还把《旧约》译为叙利亚语。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的儿子名为伊斯哈格·伊本·侯奈因,也是景教徒,除了翻译还做医生,一度接替他父亲主持智慧宫的翻译工作。他还修订、注释早期的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译作。正是靠了他的注释,阿威罗伊才读懂亚里士多德。智慧宫中有很多景教徒一点也不奇怪。在蒙古人出现之前,景教是最大的基督教分支。活动范围覆盖了从地中海东岸直到中国中原的亚洲大陆的大部分,阿拉伯帝国之初曾有两千万景教徒。旭烈兀的母亲,也就是托雷的老婆唆鲁禾帖尼(SorqoγtaniBeqi)是景教徒,旭烈兀的老婆脱古思可敦也是景教徒,本应嫁给托雷,但托雷在婚前死去,于是按照蒙古习俗嫁给旭烈兀。
早期的翻译者和学问家中有很多业余人士,所谓“民科”。他们中有医生、商人、货币兑换人(金融从业者),都是财务自由的人。最被重视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数学书,托勒密的天文书,以及盖伦的医学书。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今天还与我们同在,但天文学家兼占星家托勒密的《天文大全》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今天只有历史意义,没有科学价值。数学是永恒的;而科学是渐进的,有时可能还有革命。
现代科学史的奠基人萨顿(George Sarton)对数学史有独特的兴趣和见解,他的小册子《数学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 of Mathematics)今天看来仍然充满洞见。他称公元800年到850年这段时间为“花拉子米时代”,但早期的数学通史很少提及阿拉伯语文献。对阿拉伯语数学文献的重视程度是随着时间而增长的。1888年初版的鲍尔(Rouse Ball)的《数学简史》(A Short Account of History of Mathematics)大概是第一本用英语写成的数学史。其中把阿拉伯数学列为一章,印度数学只是这一章中的一节,这是为了阿拉伯数学做铺垫的。鲍尔把花拉子米的英文名字翻译为Alkarismi。1893年出版的卡约里(Cajori)的《数学史》中则有“中世纪”一章,第一节讲印度,第二节讲阿拉伯,第三节讲阿拉伯数学回传欧洲。卡约里还把阿拉伯人叫作“撒拉逊人”。这些早期数学史著作压根都不提中国数学。
数学史家贝尔(E. T. Bell) 1961年出版的科普读物《数学大师》(Men of Mathematics)一书按时间顺序记载大数学家的生平轶事,阿基米德之后,就直接到了笛卡尔。以霍金之名编辑的数学原文文集《上帝创造了整数》(God Created the Integers),在阿基米德和笛卡尔之间还加了个丢番图,但即使从丢番图到笛卡尔,也隔了一千两三百年。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但文明并没有因此止步。即使考虑到种族和宗教的隔阂,我们也不该忘记文艺复兴之前三百年的斐波那契吧,那可是意大利人啊,也许恰因为他的学问源自阿拉伯语文明,他的东西不被史家重视,对斐波那契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值得指出的是,丢番图的《算术》(Arithmetica)的阿拉伯语翻译是在花拉子米的书出版之后。涅尔夫妇的逻辑史权威著作《逻辑的发展》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然后就直接跳到了最后一位阿拉伯语哲学家阿威罗伊。1958年初版的斯科特(J. F. Scott)的《数学史》压根儿就没提花拉子米,只是在“东方数学”一章里,提到了几位印度数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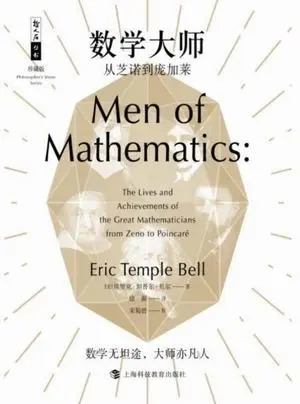
《数学大师》
美国数学史家博耶(Carl Boyer)1968年出版的《数学史》是经典,他由此被誉为“数学史家中的吉本”(Gibbon of math history)。博耶提到了花拉子米,但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花拉子米的表述是修辞性的文字表述,而不是严谨的数学表述,并且花拉子米不知道负数。他认为阿拉伯数学只是继承希腊数学,并没有太大发展。这和早期西方哲学史家对阿拉伯语哲学的看法类似。
伊夫斯(Howard Eves)的《数学史导论》在1981年出到第五版时仍然对阿拉伯人于数学的贡献犹疑不决。他提到了花拉子米,但没有仔细分析花拉子米的著作,只是把从阿拉伯语黄金时期从花拉子米到海亚姆发展出的代数,统称为几何代数,因为他们关注用几何求解代数问题。1972年出版的克莱因(Morris Kline)的大部头《古今数学思想》对花拉子米的评价就更加客气一些。但克莱因认为阿拉伯人对数学并没有在印度人的基础上推进很多。克莱因受博耶的影响很大,他的史料几乎都来自博耶。
倒是数学家或者数学家转行的数学史家对花拉子米赞赏有加。丘成桐最近研究近代数学史有心得,他鼓励岁数大的数学家研究数学史,他直言中国数学史家的著作中有义和团元素。他认为贝尔的几本数学史写的不错,但不够深,他夸赞韦伊(Andre Weil)的那本经典《数论史》,其实那本书是把数论的硬内容和有趣的数学史揉在一起讲的。最近出版的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的《素数的音乐》是科普版的《数论史》,但角度清新,非常可读。杜索托伊才五十五岁,他前两年刚接手道金斯曾担任的牛津西蒙尼(Simonyi)科普教授席位,自己也爱写科普。日本大数学家高木贞治的《近世数学史》也相当引人入胜,日本人的文笔诚恳而简洁,用来写数学真是恰当。当然,由数学家退休或半退休后改行的数学史家肯定属于被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辩》中嘲讽但同时又是心酸而无奈地叹息的“不能研究数学,只能八卦数学”的人(writing not mathematics but “about” mathematics)。但数学家们写的“八卦数学”的作品普遍比非数学出身的数学史家的作品更有洞见,毕竟是内行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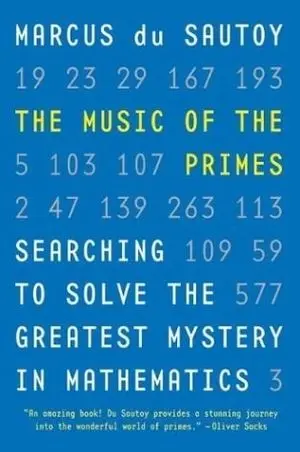
《素数的音乐》
麻省理工的数学家斯特罗伊克(Dirk Struik)的《简明数学史》尽管篇幅不长,但却是一本可以和博耶的《数学史》比肩的著作,这书1987年出到第四版,但1948年出第一版时作者就详细介绍了花拉子米的工作,是较早重视阿拉伯数学的。这书的初版在北平法文图书馆曾有收藏,解放后辗转到了中科院图书馆,只在1951年5月4日被借阅过一次。斯特罗伊克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称他的数学史研究方法是社会的。这个方法用到阿拉伯黄金时期的文明倒是恰当。左派在数学家中并不少见。斯特罗伊克是荷兰人。范德瓦尔登的老师之一曼那瑞(Mannoury),以及曾任托洛斯基保镖的逻辑学家海恩诺特也都是荷兰共产党人。斯特罗伊克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受到迫害。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援引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非美委员会的所有问题。他被剥夺讲课权利五年,但慷慨的麻省理工学院支付了他五年全额工资,直到1956年才重新恢复教职。他老人家长寿,2000年以一百零六岁高龄去世。麻省理工对待斯特罗伊克,表现得比当时其他学校逼格高,这也体现在1960年代对乔姆斯基的保护上。但当时的麻省理工校长确实宣读了对斯特罗伊克的谴责。2000年他死后,学校撤销了当年的谴责,但没有道歉。学校沉默地辩护学术自由,教授沉默地接受。
差点变成职业音乐家的菲尔茨奖得主高尔斯爵士(Timothy Gowers)主编并有一百三十三位一线数学家参与撰写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The Princeton Companion to Mathematics)是一本独特的数学读物,这本大书花了高尔斯很多精力,他亦引以为傲。天才数学家陶哲轩高度赞扬此书,说它既不像百科全书,也不像综述,也不像科普,但它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参考书,对内行外行都有用。这本《指南》的第六部分是按时间排序的数学家传记,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到布尔巴基结束,在阿基米德和笛卡尔之间,多了几位,其中就有花拉子米、斐波那契和卡尔达诺等。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花拉子米。现在流行的标准数学史教科书对东方数学的评价更加公平。卡兹(Victor Katz)分别在2009和2014出版《数学史》和《代数史》。两书都在希腊和中世纪欧洲数学之间分别加入了三章,一章讲中国,一章讲印度,一章讲阿拉伯。

Timothy Gowers
*******
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千年是西方的黑暗时期。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文明并没有断。科学史家莫勒(Violet Moller)的《知识地图》(The Map of Knowledge)干脆把中世纪知识的迁徙用不同城市按时间列出:亚历山大城,巴格达,科尔多瓦,托莱多,萨勒诺,巴勒莫,威尼斯。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复兴的突发是一个伪命题。外在地看,文明的流动是个渐进的进步过程。内在地看,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维持的高水平所持续的时间也不如希腊或者阿拉伯文明的高峰持续时间那么长。
文明的体现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所在的地域或者人口种族等载体。希腊文明从来没有中断,欧洲进入黑暗时,文明游离到了中东,载体是波斯人、阿拉伯人、景教徒和犹太人。后来到了西班牙南部、北非和西西里岛,主要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先发生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和北非较近,贸易方便。尽管文明绕了一圈回到欧洲,但载体也不再是希腊人,而是曾经的野蛮人,再后来传播到更野蛮和荒凉的西欧和不列颠岛。
文明的每一次地理上的迁移,都会经历一次大的提升。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西方哲学史家并不认为阿拉伯哲学有原创性,只是把希腊哲学阿拉伯语化了,起了接力棒的作用。现在看,阿拉伯学问,除了希腊外,还吸纳了波斯和印度的学问,融会贯通后交给下一棒。早期西方学界更加亲近在时间上更远的近邻:希腊先贤。这自然会贬低地理上更远、而时间上更近的阿拉伯远亲。远亲不如近邻。法拉比(Al-Farabi)是阿拉伯世界一位自成系统的哲学家,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和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对后代阿拉伯哲学和西方哲学影响很大,被称为亚里士多德(“首圣”)之后的“亚圣”(Second Master或Second Teacher)。法拉比在那本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举要》(Enumeration of the Sciences)中,把知识分为几个类别:1)语言;2)逻辑;3)数学与音乐,这包括算术、几何、光学、天文、音乐、力学等;4)物理和神学;5)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学。这明显传自希腊,今天的通识教育(liberal arts)也大致按这个传统。纳迪姆的《书目大全》尽管书目收录完整,但却没有法拉比那样对学科层次的洞见。
哈利利也是恨铁不成钢,他在《智慧宫》最后一章中讨论了为什么阿拉伯没有和现代科学沾边。这个问题在阿拉伯知识分子中,犹如李约瑟之问在中国。从文明迁徙的角度看,对李约瑟问题倒是可以有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回答:东亚离文明的中心太远,没机会加入文明的大循环。在动荡不安的年头,放大时间颗粒度,能够为人类取得的成就自豪,从而增添一些乐观的精神。
********
现代一元二次方程的表达式是 ax2 +bx + c = 0。花拉子米不知道负数,于是他给出了一元二次方程的六种可能形式,
1. ax2 = bx
2. ax2 = c
3. bx = c
4. ax2 + bx = c
5. ax2 + c = bx
6. bx + c = ax2
这里a, b, c都是正数。花拉子米当然也不知道还有复根,其实现在的初中代数也不讲复数。
华裔学者罗博深(Po-Shen Loh)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数学教授也是美国奥数队的教练,他在2019年底给出了一个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更简单快速的解法,曾经引起热议。把古老的东西玩出新花样,挺有意思。
有些人把花拉子米的代数贴了“几何代数”的标签,因为花拉子米的解用到了几何方法。拉希德不喜这种说法,他认为花拉子米不懂希腊文,肯定知道《几何原本》。花拉子米代表了波斯的数学传统,他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是反希腊的。后人对花拉子米轻视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代数书的目的就是实用,而不像希腊数学那么纯粹。后来通过斐波那契传到新欧洲的阿拉伯数学的主要是为了贸易记账。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辩》中说数学家研究数学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实用,大部分数学是不实用的。但我更喜欢物理学家尤金·威格纳(Eugene Wigner)的文章“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in Natural Sciences”,对自然科学,数学就是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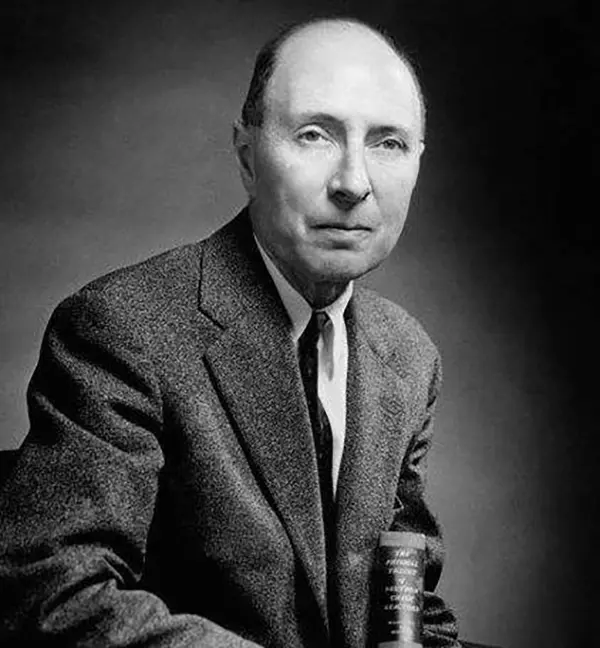
Eugene Wigner
关于花拉子米的历史记载太少,我们无法想象他的日常生活。智慧宫的人肯定吃喝不愁,生活优越,但是数学家肯定不仅仅坐在智慧宫里算题。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占星术士被当作一类人,有时也要接些体力活儿。花拉子米就曾带队去做过野外测量。这有点像高斯,他也曾很不情愿地主导过汉诺威公国的大地测量。数学家曾经是既劳心又劳力的职业。黎巴嫩裔法国历史学家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的历史小说《撒马尔罕》说的是波斯数学家兼诗人卡亚姆的故事,里面有爱情、生死和暗杀。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史》只写了三位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为首,二百五十年后的卡亚姆为尾。卡亚姆数学成就之一是用双曲线求解一元三次方程,可算得花拉子米开创的阿拉伯代数的继续,但他的诗集《鲁拜集》更广为人传颂。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本被认为有二次创作之嫌,从中随机摘取一首:
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did I sow,
And with mine own hand wrought to make it grow;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d –
“I came like Water, and like Wind I go.”
郭沫若的中译:
我也学播了智慧之种,
亲手培植它渐渐葱茏;
而今我获得的收成——
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转载请超链接注明:头条资讯 » 尼克︱花拉子米和智慧宫:代数一千二百年
免责声明
: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