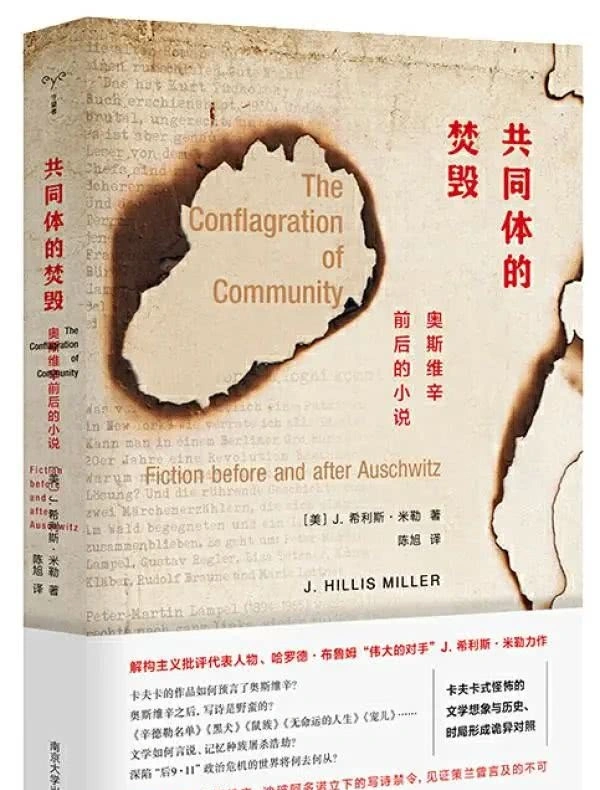
J.希利斯·米勒的《共同體的焚燬: 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原書名: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2011;陳旭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是一部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該書深刻動人……它邀請讀者嚴肅對待我們最迫切的擔憂,同時每一頁都在勸誡讀者嚴肅對待文學。”(朱利安·沃爾弗賴斯)這位評論者把它的文學批評意義與關於時代的現實關懷聯繫起來,對於我們來說這已然是很充分的閱讀理由。
既然是討論奧斯維辛與文學的關係,西奧多·阿多諾的那句名言自是繞不開的。那句廣為流傳的格言原話是:“奧斯維辛之後,甚至寫首詩,也是野蠻的。” 阿多諾後來自己做了修正:“說奧斯維辛之後不能寫詩或許錯了”,而米勒則嘗試對這句話的措辭做多種角度的闡釋: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這個行為動作是野蠻的;為了確保類似悲劇不會再次發生,寫詩無濟於事,我們無暇超然於政治之外;另外,“野蠻”(barbaric)這個措辭也值得注意,阿多諾認為在黑暗的日子裡詩歌是無意義的音節,就像是野蠻的“巴、巴”聲中的胡言亂語。總之,米勒力圖回到阿多諾說這句話的語境:並非指當時寫詩是野蠻的,而是指當時堅持文化批評已無可能,因為整個社會都空洞墮落,文化批評頃刻間就與它要批判的對象形成共謀,有淪為無關痛癢的嘮叨的危險。(“前言”,第1—3頁)當然,很多作家無視阿多諾的充滿倫理意味的禁令,於是才有了“大屠殺文學”。米勒認為阿多諾“沒有意識到文學是見證奧斯維辛的有力方式,無論那份證言可能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文學本身成為見證,特別能夠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些逝去的超過六百萬的生命,並由此指引我們從記憶走向行動”(第4頁)。他和許多人一樣認為納粹大屠殺事件是人類歷史上的轉折點,但他更強調的是“不以史為鑑,註定要重蹈覆轍”,因此他在書中一再提到寫這部著作不僅是一項學術工作,更是一種道德責任。
這部副標題為“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的文學批評著作有著極為深刻的、前瞻性的和雄心勃勃的意圖:第一,實際上它也是一部文學社會學的著作,在所討論的八部文學作品之上高懸的是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所關注的“共同體問題”;第二,以這些文學作品為視角所串聯起來的景觀是近現代歷史研究的重大論題(美國的奴隸制、納粹大屠殺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政治);第三,在方法上,它把後現代理論中的“共同體”觀念與文學文本中的共同體敘事貫通起來,把文學創作與閱讀及批評的目的性與可能性放置在各種複雜的歷史語境和極端時刻中予以重新審視;第四,它在解構主義的批評背景中堅持文本細讀與歷史考證的雙重路徑,最後是把文學、歷史、現實及未來融為一體。不得不讓人佩服的是,這部著作出版的時候米勒已經是八十三歲高齡,他不僅表現了敏捷、開闊的視野和周密、深邃的文本細讀技巧,同時還表現出對大屠殺與文學敘事的關係有了更多的審慎判斷和真誠的自我反思。
在質疑了阿多諾關於奧斯維辛與詩歌的言論之後,米勒把他的寫作意圖講得很清楚:“我試圖將幾部明顯指涉大屠殺的小說與其他奧斯維辛前後創作的作品聯繫起來,在近來研究大屠殺對構建共同體的影響的理論視野中,探究上述作品的共性。我認為卡夫卡的作品預示了奧斯維辛,凱爾泰斯的《無命運的人生》迴應了卡夫卡,而莫裡森的後奧斯維辛小說《寵兒》具有卡夫卡小說的特徵。在我所言及的作證的意義上,儘可能地細讀這幾部小說,這是我首要的關注點。”(第7頁)從該書的敘述框架來看,米勒首先用了很多篇幅討論從史蒂文斯詩歌中的共同體思想到讓-呂克·南希、德裡達、德勒茲等哲學家闡發的共同體理論及相關論述,反思何謂“共同體”以及“共同體的焚燬”;接下來討論了從卡夫卡的三部預示了奧斯維辛的小說到託馬斯·基尼利、伊恩·麥克尤恩、阿特·斯皮格曼和伊姆雷·凱爾泰斯分別創作的四部關於大屠殺的小說,再到莫裡森的《寵兒》,一再把“共同體的焚燬”與德國納粹上臺的歷史時刻以及美國在千禧年之後的國內外形勢結合起來,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文學創作中的預感、見證和今天的閱讀者所肩負的道德責任。
米勒在書中對布什政府的國內外政策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性,這一點曾引起爭議,似乎大可不必在文學批評中加入份量如此之重的現實政治批判。其實,在研究和討論奧斯維辛與文學、納粹政治與人類命運的時候,怎麼能設想和容忍對現實政治的麻木和冷漠?米勒說,“我現在讀卡夫卡時,內心深處難以平靜,不僅僅是因為我感到自己遇到了無法控制的怪怖因素——這些因素甚至也可能超出了敘事學的闡釋範圍,還因為我有一種不安感,我感到現在生活的世界,與卡夫卡《城堡》的世界更為相似,其相似度遠超其他任何我所知的虛構作品的作家所創作的世界。我想到了喬治·W·布什任下的美國治理。在那些被選出或任命的官員中,許多人幾乎罔顧現實,常常滿口謊言,背信棄義,甚至是徹徹底底的罪犯”(139頁);“在布什執政的日子裡,每個美國人都有可能像約瑟夫·K那樣,聽到敲門聲後,無辜被捕,經歷一系列噩夢般的找尋,卻找不到那條據稱被自已違反了的法律,不知道指控者是誰,沒法依法與其對質。審判或曰‘過程’就有可能在公認的官方判決下達之前,被推向秘密處決的高潮。《審判》中約瑟夫·K的經歷預示了布什任期內我們的處境。為何在如此駭人的事情發生之前,公共輿論沒有強烈抗議,大街上沒有遊行,作惡者沒有遭彈劾,以拯救我們寶貴的民主制度及其憲法根基?取而代之的是散見於報紙和電視新聞的冬星消息,除了集體表示聳聳肩之外,修改《監視法案》幾乎沒激起任何反應。”(98頁)無論米勒所描述的布什時代的政治形勢是否全面和準確,他的不安與批判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米勒這部文學批評著作的第一關鍵詞是“共同體”,這與文學和文學批評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共同體的焚燬”究竟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文學敘事和文學批評的預感與見證均與“共同體的焚燬”有密切關聯,因而成為米勒在該書中深入研究的議題?米勒把“共同體”這個概念作為一條連結大屠殺與文學敘事的路徑,他對“共同體”的描述是“這些主體和其他主體為了公共利益結合在一起,他們相互交流的模式可被稱作主體間性,這種交流是主體交互的通道,假定了他者與我一樣。”(17頁)但這是一個神話。當一個從集中營歸來的囚犯表示不想控訴納粹的時候,他的猶太親戚被他的態度深深激怒,覺得這不是“我們”應有的立場和態度。(《無命運的人生》)米勒從這裡看到共同體其實並不存在,這對於也經常把“我們”掛在嘴邊的“我們”來說,不也是一種警醒嗎?在討論莫裡森的小說《寵兒》的時候,米勒指出小說所涉及幾個不同的共同體背景:南北戰爭是美國這個共同體的一場內部戰爭;蓄奴的南方社會也是一個由白人奴隸主和黑奴的共生及奴役與恐懼關係構成的共同體;南方黑人又是一個“共同體”結構,內部也是撕裂的:一方面是因為支離破碎的黑人家庭,另一方面是奴隸群體可能發展出的任何團結一致的情感都會因其對白人構成威脅而遭到系統性破壞——這種對共同體的刻意破壞是奴役者、殖民者和帝國主義徵服者的常見行為。(312—314頁)在米勒看來,辛辛那提黑人共同體與其自身的關係是《寵兒》的主要議題。如果說從政治學的共同體理論和文學的敘事理論、批評理論中思考還真有點費勁的話,從我們當下的經驗、感受中可能更容易獲得真切的認識——原來我們以為的某種“共同體”其實不堪一擊,就像米勒發出的質疑:“共同體真的存在嗎?”、“是什麼東西摧毀了共同體?”雖然我們早已不相信有什麼共同體的存在,但是我們對“共同體的焚燬”及其後果——對劫難的預感和見證——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呢?
米勒在卡夫卡、凱爾泰斯、莫裡森等人作品中發現了共同體想象的“焚燬”,因而傷害與苦難必然會到來,這些文學作品肩負了預感與見證的使命。問題是,從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對大屠殺的預感、預言,是否有確鑿的證據?會不會是今天的文學批評家以後見之明推論的結果?如何區分文學批評中的如實揭示與主觀推測?米勒在第二章“卡夫卡作品中的奧斯維辛先兆”中回答了這些問題,他的方法是文本細讀與歷史考證。前者是他的拿手好戲,解構批評對於文學語言有獨特的關注,修辭性閱讀就建立於細讀的方法之上,而米勒細讀文本的功夫更是非同尋常;後者涉及使用各種歷史資料以進入歷史語境,完成與文學作品的邏輯互證。七十年代後期,耶魯大學的一批文學批評家掀起一股後結構主義批評思潮,希利斯·米勒就是所謂的“耶魯四人幫”(“耶魯四君子”)之一。到了晚年的米勒不但可以說寶刀未老,而且更有出色的表現。在該書的文本細讀部分,隨處可見的是技術性語言與文本語言的水乳交融、彼此激發,在文本的“縫隙”裡發掘潛在文本、暗語,理論術語也非常貼合地進入了闡發之中。而老先生對於文學批評本身的反思,惴惴於文本批評與大屠殺研究之間倫理錯位,更是令人深思。
在文本細讀之外,米勒對圖像證史也極為重視。他在前言中特地講述他如何從網絡上查閱各種歷史照片:“有卡夫卡及其家庭的大量照片;有關於奧斯維辛的照片,其中包括最近發現的卡爾·赫克爾(Karl Hoecker)相冊樣照;有記錄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系列影像資料……有大量反映美國私刑的照片,許多最初以明信片的形式傳播;還有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這些照片都是作證的一種形式。……受現實所限,本書無法收入所有相關照片,但書中附上了對我思考和寫作最為重要的那些照片的URL地址。能上網的人都可以找到這些照片,看它們如何見證。我敦促讀者們都去見證。”(“前言”,第8頁)可惜的是中譯本連一張作為插圖的照片都沒有。米勒在書中對那些照片的描述充滿了悲憫,令人動容:“從受害者乘火車抵達奧維辛,經過遴選,直至被殺,女人、孩子和那些被判定為不夠健康男人毫不知情地在毒氣室門口排隊等候,這一進程的所有事件都有詳細的照片記錄。這些照片最可怕的地方在於,這些受害者仍然不知道幾分鐘後將要發生什麼。”(63頁)而另一種照片則令人更加不安和深思:“更讓人心情不能平靜的可能是那些記錄納粹黨衛軍軍官在屠殺間歇嬉戲放鬆的照片。所謂的卡爾·赫克爾相冊收集了這些熙片,即將出版。赫克爾在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任奧斯維辛指揮官的助手。……美國一位軍人在奧斯維辛解放後把赫克爾的相冊帶回了美國,直到最近他才把這本相冊交給美國當局。這些照片讓人寢食難安,因為照片上的這些壞人,包括他們的秘書和情人這些‘幫手’在內,看起來都那麼普通,那麼開朗。他們儘管罪惡滔天,但看起來就像普通的德國軍官及其漂亮的女朋友。……我強烈建議本書的讀者去網上搜這些照片。”他還提到了關於美國奴隸制和黑人解放後仍遭受私刑的照片,在南北戰爭後的數十年間,這些照片在南方廣為流傳。(96—97頁)米勒對歷史照片的重視來自他少年時期的難忘印象。“我對集中營的有限瞭解始於少年晚期,當時集中營解放了。我仍然記得那些可怕的照片,屍體層層堆疊,倖存者骨瘦如柴——如果沒記錯的話,我是在《生活》(Life)雜誌上看到的。我當時相信,當然現在仍然相信,這些照片是真實的證據。我能夠作證,我見過這些照片。”(185頁)這也可以看作是對我們今天的歷史圖像學研究的一種激勵。
米勒在“結束語”中把文學是歷史的見證作為該書的論述前提之一,他說“小說作為有效的見證,其作者越接近小說要間接見證的歷史事件,其敘事就會越複雜。”(327頁)所謂“接近”與“複雜”,在我看來還可以別有深意。閱讀宗教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在最嚴酷的歷史時刻,比如十六世紀英國教會史家約翰·福克斯的《殉道史》( 蘇欲曉、樑魯晉譯,三聯書店,2011年 1月)所描述的西方教會史上的壓迫、受難語犧牲的時刻,見證者也是殉道者(在希臘文中的“殉道者”的原意就是“見證者”)。殉道者不僅為信仰而受難,而且還為對這種受難的見證而受難。這不是最為“接近”和需要最為複雜的敘事的時刻嗎?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詩的見證》(黃燦然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年11月)的第一講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時代,我們老是聽人說,詩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後重寫的羊皮紙文獻,如果適當破譯,將提供有關其時代的證詞。”;“顯然,我是在思考詩歌正在確立什麼樣的證詞來見證我們這個世紀,儘管我明白,我們仍然浸染在我們的時代中……。”(15頁)然而,為什麼首先是詩,而不是別的最有資格為時代作證?他說“詩歌的見證要比新聞更可靠。如果有什麼東西不能在更深的層面上也即詩歌的層面上驗證,那我們就要懷疑其真確性。”(22頁)預感與見證的關係有時是十分殘酷的,米沃什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羅斯有過最令人沮喪的預感,而這種預感則在“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瑪託娃溫聲細語的詩中”得到見證,詩歌因此而成為歷史的見證。他說二十世紀的詩歌見證了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存在著嚴重的混亂,能意識到這一點才有自我療救的希望。從宗教到詩歌,這些不都正是米勒的預感、見證理論所闡述的真理與道德責任嗎?
米勒在“中文版序”說,“我留給中國讀者自己去探索,看看你們能從《共同體的焚燬》中讀出些什麼”。我們究竟應該或能夠如何回答?——當然,沒有“我們”,只有“我”或“你”。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一週書記:文學批評所揭示預感和……見證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