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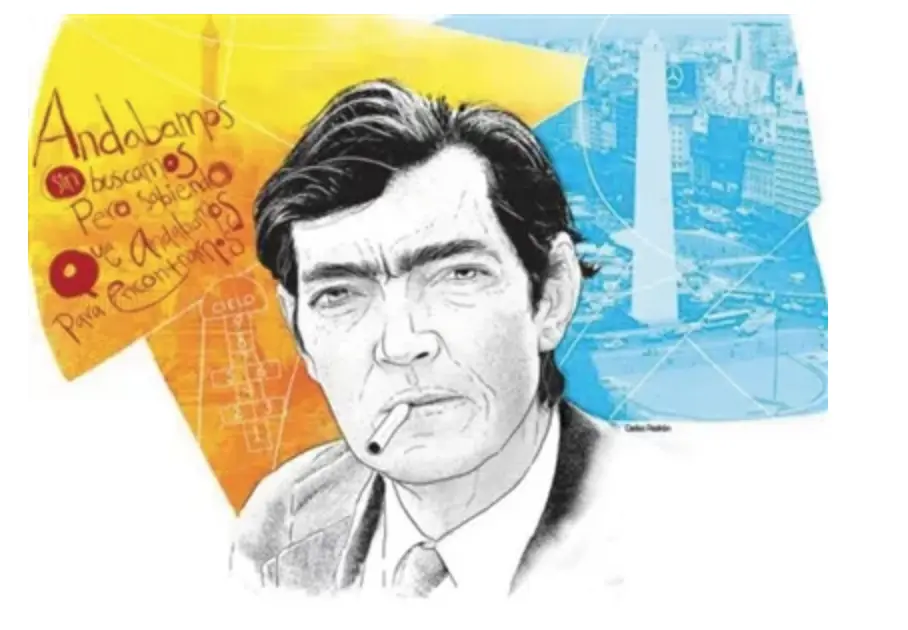
胡里奧·科塔薩爾1914年出生於比利時。6歲時,他的父親離開家庭,從此音訊全無。他的童年在母親與妹妹的陪伴下度過,這一點也呈現在他的小說中。
童年的科塔薩爾體弱多病,只能每天面色蒼白地躺在病床上閱讀小說,再加上他討厭吃大蒜,所以被周圍的朋友們起了個“吸血鬼”的外號。
科塔薩爾對這個綽號欣然接受,還真的裝模作樣扮演起了吸血鬼的樣子。他當時躺在床上閱讀的書籍也不乏恐怖故事、偵探小說等等,這種遊戲的心態伴隨了科塔薩爾的一生。
在去世前不久的採訪中,69歲的科塔薩爾依舊認為自己的真實年齡只有10歲。他的小說也天真而充滿樂趣。但在科塔薩爾令人著迷的遊戲文本背後,也有著他因政治與革命而誕生的反思與痛苦。
1
文學的頑童
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索曾在《文學“爆炸”親歷記》中記載過一件軼事。他邀請了很多拉美作家來家中做客
(幾乎所有拉美作家都互相認識並且熱衷於對“文學爆炸”這個貶義稱呼以及拉美革命的討論)
,外面下著白色的雪,作家們則因為嚴肅的政治討論而面紅耳赤,接著外面傳來一陣喧鬧聲。他看到胡里奧·科塔薩爾正在和另一位拉美作家打雪仗,他們彼此把雪球扔到對方的臉上並樂在其中。多諾索說科塔薩爾的兜裡還會裝著遙控賽車,在聚會的間隙拿出來和其他人較量較量。
“對我來說,文學是一場遊戲,”科塔薩爾說道,“但它是一場可以讓你畢生投入的遊戲。你可以為了玩好這場遊戲去做任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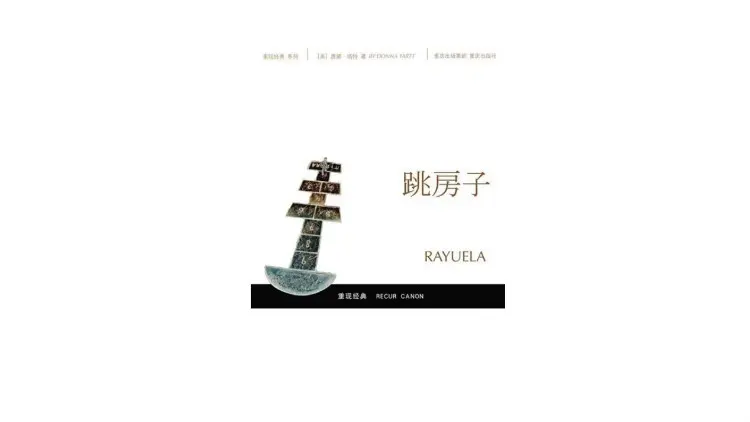
《跳房子》,科塔薩爾著,孫家孟譯,重慶出版社,2008年1月
這種遊戲文學最極致的表現則是科塔薩爾的長篇代表作《跳房子》。他完全打破了敘事中的時空聯繫,用多種聲調講述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巴黎和蛇社之間的故事。他不僅在小說的最後附上了作家本人推薦的閱讀順序表,還聲稱期待著讀者自己能找到第三種,第四種,乃至第無限種閱讀方法。1963年,這本書成為了阿根廷青年爭相閱讀的著作,但它並沒能成功走向世界。歐美出版社不敢購買這本書,也不敢購買科塔薩爾其他短篇小說的版權,他們覺得出版這樣一個打破教條、在小說藝術上完全另起爐灶的作家過於冒險。
相比於長篇小說在結構上的遊戲性,那些短篇小說的敘事遊戲性更強烈,或者說,它們本身就是遊戲。只是,隨著敘事節奏的進行,支撐著小說敘述的遊戲規則潛行到某個階段後,突然鑽出水面,讓讀者發現這並不是簡單的遊戲,而是某種指向現代生活的、極具嚴肅性的東西。比如,在《給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那個男人走在公寓的一樓和二樓之間,突然張嘴吐出了一隻兔子。怪誕的行為被科塔薩爾筆下的主人公完全接受,那個男人看著手中的兔子,不僅覺得它可愛,而且覺得溫暖,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從體內吐出的東西帶有某種象徵著不安的意義。“安德烈婭,習慣是節奏的具體表現形式,是節奏的一部分,幫助我們生活。一旦進入固定不變的循環週期,一切條理化,吐出兔子就沒那麼可怕”。
但是當這個男人吐出第十一隻兔子時,故事的娛樂性終結了,他開始無法接受生活的遊戲規則了,取而代之的是嚴肅的悲觀主義。“可是十一隻不行,因為,安德烈婭,有十一隻就有十二隻,有十二隻就有十三隻”。《被佔的宅子》中,我和伊雷內所居住的房間被莫名的東西佔據,但他們還能在裡面織毛線、喝馬黛茶,直到這個節奏進展到整座宅子都被佔據,他們無處可去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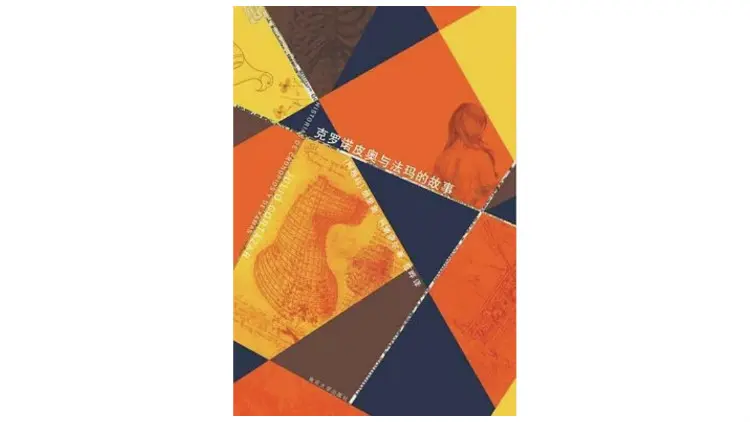
《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科塔薩爾著,范曄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
基本無一例外,這些短篇故事都在科塔薩爾內心醞釀了很久。其中有些直接來源於夢境
(由於小時候體弱多病,科塔薩爾只能躺在床上養病讀書,白天閱讀凡爾納,愛倫·坡,雨果,晚上就做噩夢)
。他的創作過程聽起來很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這或許是他在法國巴黎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翻譯員時獲取的藝術啟示。但夢境在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裡只是構成氛圍,將夢與潛意識直接描繪出來的作品會極具私人性且難以理解。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則從開頭就能讓人感受到一個悲劇正在揭幕--酒吧裡一個男人心碎地講述著一個陌生人正在重複著自己乏味的命運;一個人被父母逼迫著去迎接並不喜歡的人;卡洛斯叔叔帶著滅蟻器去花園裡消滅螞蟻;一對夫妻要照顧一種名為芒庫斯比亞的動物……悲劇在這些故事中被不斷延宕,好像有種更凝重的生活氛圍在暗中保護著它。這種暗中掩飾著生活悲劇的東西,正是現代生活
(或者說科塔薩爾為小說設置的遊戲規則)
自身的節奏感。
“如果日子只是機械重複,毫無變化,也許,我說的這些也就千篇一律,毫無用處。”科塔薩爾在《劇烈頭痛》中寫道。科塔薩爾的這些短篇小說,理應在現代更加受到讀者的歡迎,因為這些小說的氛圍與捕捉到的生活節奏要比人物與故事本身更重要。
2
遊戲的終結
《動物寓言集》和《遊戲的終結》都是科塔薩爾創作於20世紀50年代的作品。1963年,科塔薩爾訪問了古巴,從那之後,對古巴革命的政治興趣開始影響他的寫作。“三十年前,當我把自己的構思付諸筆端時,我只用審美的標準進行評判。現在,儘管我還用審美的標準來進行評判,因為我首先是一名作家--但如今,我是一名分外關注拉美局勢,併為之感到苦惱的作家;因此這一點常常有意無意地流露到筆端。”1984年,他在接受《巴黎評論》的採訪時說到。
阿根廷與古巴的社會發展截然不同。前者是拉美地區最具多元化,最現代化的地區。這種社會背景時常讓作家們忘記自己是阿根廷人,即便是阿根廷的政治氛圍開始發生轉變,庇隆主義與軍政府主義開始接收國家的時候,他們依然可以選擇前往瑞士或法國避難。即便留在阿根廷國內,也可以從博爾赫斯溫和的圖書館與私人主義中得到自由的慰藉。而古巴則不同。在20世紀的拉美地區,只有墨西哥與古巴經歷過徹底的社會革命。發生在鄰國的事件自然吸引了科塔薩爾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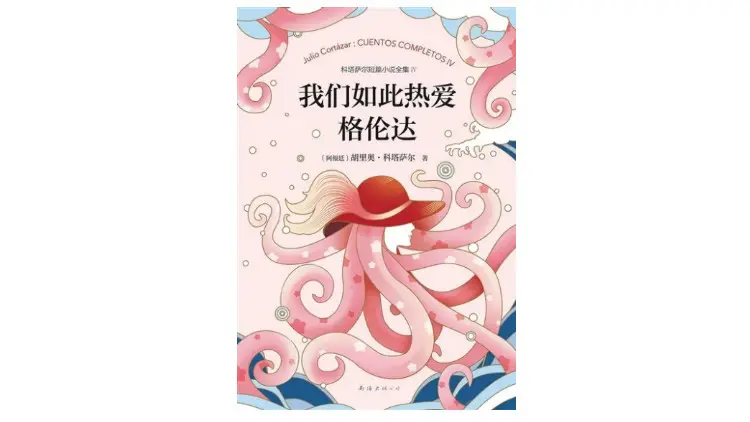
《我們如此熱愛格倫達》,科塔薩爾著,陶玉平譯,新經典 | 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11月
在最新譯介的短篇集,《我們如此熱愛格倫達》中,這種關乎政治的現實傾向更加明顯。其中,很多觀點都體現在創作於1979年的《某個盧卡斯》中。1977年,他的小說集《有人在周圍走動》出版後也遭到了阿根廷軍方的審查。這種傾向很明晰,但並不明顯,科塔薩爾在距離政治與革命更近的文學創作中依舊保持著一貫的遊戲性,有許多故事的遊戲規則和他早期的作品十分相似,區別在於,在早期的故事中,一個主人公發現照片上拍出來的東西和他看到的不一樣,由此指向了對人生真實性的質疑;而在後期一個類似的故事中,主人公拍了一張某地區的照片,沖洗後發現照片裡反映的城市景觀比他肉眼所見的更復雜,由此指向了對社會真實性的反思。
在這段時期,科塔薩爾的很多信件、雜文與採訪都凸顯了他對古巴革命的迷戀,左翼知識分子反抗極權政府,聽起來像是在為拉丁美洲開闢一個光明未來。他也想用小說表述自己對此的支持。不過即使是在這些作品中,這種政治的隱喻依然相對隱蔽。例如,科塔薩爾的中文譯者范曄曾經解讀過經典短篇《美西螈》的寫作背景,這個故事如果只從純審美的角度閱讀,很類似於里爾克的《豹》,藉助巴黎植物園內動物的軀體與特殊狀態勾勒出個體的精神困境——“我又看見了它的眼睛、它的臉。毫無表情的臉上,除了眼睛再無其他器官。那雙眼睛,就是兩個如大頭針頭般的孔洞,完全是一片透明的金黃色,恍若死物,卻仍在瞪視著周遭”。但聯繫到這個短篇的寫作背景,它卻表現了科塔薩爾本人的自我分裂,一個自我是詩人的,玻璃櫃外的,而另一個則在水族箱內,距離很近,卻又觸不可及,猶如身在阿根廷的他對古巴革命的情感。
科塔薩爾的小說有強烈而一以貫之的風格,但在沉浸於古巴革命之後,他的短篇小說再也沒有重現原初的驚豔,彷彿一個充滿天賦的孩子在成年後失去了天真與靈性。
1984年,科塔薩爾在巴黎去世,死因一說為白血病,另一說為死於輸血時感染的艾滋病。他去世後,拉美地區一直不乏對他的紀念活動,以他的姓氏為街道與學校命名,在百年誕辰時研討科塔薩爾的文學作品,有人說他是堅定的左翼知識分子鬥士,有人說他用創新的短篇形式反抗暴力,有人說他的作品裡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新觀念和烏托邦的可能性。
但在《科塔薩爾論科塔薩爾》中,他說,“一本書早在它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寫完之前和寫完之後就開始和結束了”。
作者|宮照華
編輯|張婷
校對|趙琳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科塔薩爾:如果生活非要千篇一律,我就把它寫成遊戲!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