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繪畫史領域中,“逸品”是一個唐代畫論中出現的名謂,且觀點一直在延續和發展。初唐李嗣真、中唐朱景玄、北宋初黃休復、北宋徽宗趙佶(1082—1135)、明代王世貞(1526—1590)、董其昌等都有過“逸品”說。“逸品”這一名謂流變的脈絡,大多集中於早期“逸品”的概念和晚期文人畫範疇內的變遷這一問題上。西方對“逸品”的關注大致始於20世紀前期,“逸品”這一問題,貫穿了西方對唐代“潑墨”、禪畫、文人畫觀等各類畫史範疇的理解,值得作一梳理。本文著重於觀察這一畫史概念在西方的生成和理解。
在中國繪畫史領域中,“逸品”是一個唐代畫論中出現的名謂。根據胡新群在其博士論文《唐宋繪畫“逸品”說》中的整理,自唐至清,“逸品”觀點一直在延續和發展,經歷初唐李嗣真(不詳—697)“超然逸品說”、中唐朱景玄(活動於841—846)“格外逸品說”,北宋初黃休復(活動於1005年前後)“首推逸格說”、北宋徽宗趙佶(1082—1135)“神逸妙能”四品說、鄧椿(活動於12世紀)“逸神妙能”四品說等。明代有王世貞(1526—1590)“逸品說”、董其昌(1555—1636)再次推重“逸品”;清代又有惲格(1633—1690)“逸品說”。
同時,關於“逸品”這一名謂流變的脈絡,已有多位學者作過研究,大多集中於早期“逸品”的概念和晚期文人畫範疇內的變遷這一問題上。如徐復觀先生認為,“逸格”自元季四大家出,始完全成熟。真正的大匠很少以豪放為逸,乃多見於從容雅淡中。學者鬱火星在《論逸品畫的藝術特徵》一文中,認為“逸之品格”包括“奇”“變”“自然”“簡”“雅”“清”“淡”“高”“遠”等,又或者“逸筆”“逸氣”“逸畫”構成了“逸”的有機整體。胡新群則認為,朱景玄首倡“逸品說”,蘇軾及鄧椿力倡“逸品說”,是中國繪畫“寫意”畫風與畫法形成之理論依據,亦即“逸品”與“寫意”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西方對“逸品”的關注大致始於20世紀前期,在喜龍仁1936年的著作《中國畫論:自漢代至清代》已能見到端倪。喜龍仁在著作中提到,在將畫作和畫論分類時,古人經常在神、妙、能三類之外,再加上“逸”(i)這一類,指的是最為純出自然和解放天性之作,而不從屬於任何類別的畫家。然而“逸”和其他品類之間的關聯卻並不清晰。喜龍仁看到,朱景玄將“逸品”作為“神”“妙”“能”三品的補充(appendix),並將黃休復畫論中的“逸格”翻譯為“天然風格”(the spontaneous style),由此可見,究竟如何定義“逸品”和如何看待它的生成和變遷,對作者來說還並未經過深入的思索和辨析。事實上“逸品”這一問題,貫穿了西方對唐代“潑墨”、禪畫、文人畫觀等各類畫史範疇的理解,值得作一梳理。本文並非旨在重複闡述“逸品”之涵義,而是著重於觀察這一畫史概念在西方的生成和理解。
一、島田修二郎《逸品畫風》的研究與翻譯
日本學者島田修二郎(1907—1994)於193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在獲得博士學位前後,他陸續開始發表論文,逐漸奠定了他在中日繪畫史研究界中的一流學者地位。島田在日本漢學界中屬於“京都學派”,重訓詁、考證,學風嚴謹。1962年,他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與考古學系教授,成為了美國大學中第一個設立日本藝術史專業之人,對西方瞭解東亞藝術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圖1)

圖1 喜龍仁(中)與日本藝術史家島田修二郎(右一)在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看中國古畫
西方學者對中國畫論中“逸品”的深入瞭解,始於島田修二郎1950年發表在日本《美術研究》上的《逸品畫風》一文。美國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4—2014)將其譯成英文,名為“Concerning the I-P’in Style of Painting-I”,分成三部分,分別發表在《東方藝術》(Oriental Art)1961年第2期(圖2)、1962年第3期和1964年第5期上,在西方學界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本文選用的版本主要是高居翰譯文和1991年臺北《藝術學》輯刊翻譯的《逸品畫風》中文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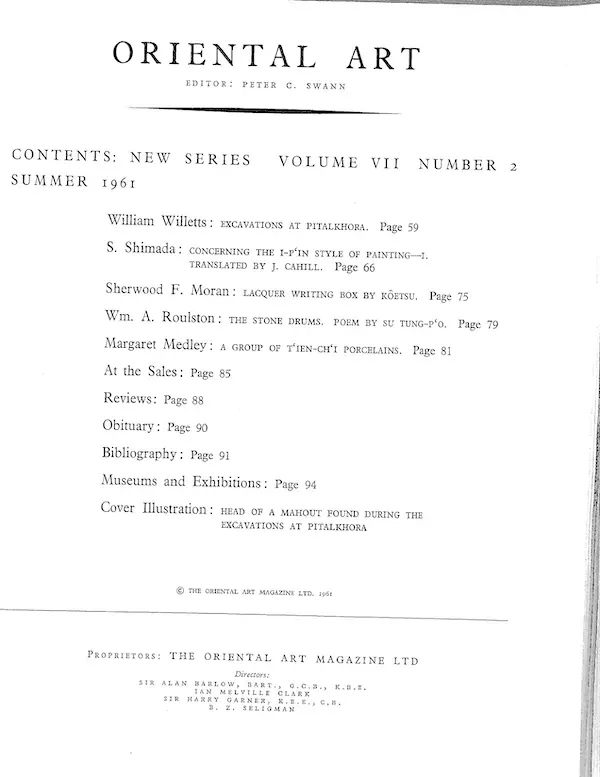
圖2 1961年的《東方藝術》(Oriental Art)刊出《逸品畫風》英譯篇的目錄

圖3 高居翰
在文中,島田首先介紹了“逸品”出現的歷程,從謝赫(479—502)、顧愷之(348—409)等魏晉畫家的三品九等之法,到唐代張懷瓘(活動於713—741前後)分“神、妙、能”三品,再到李嗣真定出畫中逸品,晚唐朱景玄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又加上“逸品”,即“在其格外,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優劣。”,作者籍此將“逸品”相對於另三品的地位定義為:“具有超越畫之本法,即一般所認定的正常畫法的這一畫風之畫。……因此,所謂的神、妙、能、逸的四品等第,並不是同一性質序列的排列,而是將逸品視為一種與依於正統畫法而來的神、妙、能三品的相互對立,且又在另外設立的一種奇逸畫法。”
就畫家而言,島田認為,從朱景玄所定逸品中的三人,王墨(不詳—805)、李靈省(活動於806—820前後)和張志和(732—774)中,至少有二人處於中唐時代,朱景玄本人則是中晚唐時代人,可以見出“逸品畫風”大約是從中唐時代開始確立的。王墨和李靈省都採用“潑墨”“一點一抹”的即興作畫法;顏真卿《文忠集》卷九《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錄》中載,張志和的醉後作畫也頗為接近王墨,即“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俄揮灑橫抪,而織纊霏拂,亂槍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 但類似王墨的潑墨法,在當時的正統畫論,如《歷代名畫記》卷十“唐朝下”中則頗有微詞,謂之:“雖乏高奇,流俗亦好。……然餘不甚覺默畫有奇。”另《歷代名畫記》卷二“(吹雲法)此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如山水家有潑墨,亦不謂之畫,不堪仿效。”張彥遠在此提出“不見筆蹤”,未必是後世所理解的一般意義上的“筆法”,而是按照物象運筆作畫的行為。因“吹雲”等畫法並未使用畫筆,而是採用其他媒介隨機畫出。島田修二郎由此概括出“逸品畫風”的基本性格:
即在緊密的筆法要求上,取以粗放,然缺骨氣,在象形上,沒有明確的輪廓,然卻有顯著變形化、與簡略化的自然形態。此等若以當時的正統畫風作為基礎來考量,或者傳統繪畫觀上的六種規律原則,亦即是畫之六法作一比較參照的話,可發現那是對骨法用筆之法的忽視,同時亦是對應物象形的違反。
換言之,“逸品畫風”是不承襲“應物象形”和“骨法用筆”的風格,具體來說即兼具“簡略”(abbreviation)和“粗筆”(rough brushwork)的創作。在定義了“逸品畫風”的樣貌之後,島田修二郎繼續追溯這類畫風的源頭,認為可以上溯到隋代好畫“魑魅魍魎”的孫尚子(生卒年不詳),盛唐以前的“跡簡而粗,物情皆備”的張孝師(生卒年不詳),再到中唐的張璪(生卒年不詳)、韋偃(活動於8世紀)等。如《唐朝名畫錄》中載韋偃“思高格逸”“山以墨斡,水以手擦,曲盡其妙,宛然如真”,與王墨潑墨畫法有相似之處。王墨學自項容,因荊浩(約856—不詳)《筆法記》記項容“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然於放逸,不失真元氣象。”因此,項容也具有“逸品畫風”。島田認為,由諸多文獻記載可知,水墨畫在中唐的出現,以及和“逸品畫風”的結合,是以山水畫作為舞臺而伸展開來的。
島田繼續敘述道,到了北宋的景德年中(1005),出現了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輯錄了自唐代乾元初(758—759)到宋初乾德歲(963—968)共58位蜀地畫家。與朱景玄將“逸品”置於其他三品之後相反,黃休復將“逸格”置於最高的地位,且只選取了唐末孫位(活動於9世紀)一位畫家。島田發現,與朱景玄一樣,黃休復所認為的“逸格”也具備簡略之風。在《畫繼》中,又列出了石恪(活動於965—975前後)和貫休(832—912)二人,並稱:“然未免乎粗鄙”“意欲高而未嘗不卑”。石恪的“逸品畫風”,在元代湯垕(活動於14世紀)的《畫鑑》中則載為“戲筆畫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麄筆成之。”與曾收藏於日本正法寺的模寫本《二祖調心圖》(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風格相似(圖4)。同樣,高臺寺所藏的貫休的《十六羅漢圖》(圖5)和分藏於日本的其他殘本,也屬類似的“逸品畫風”。

圖4北宋,石恪,《二祖調心圖》,紙本水墨,35.5x129釐米,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5 五代,貫休,《十六羅漢圖·諾距羅》, 絹本設色,129.1x65.7釐米,日本高臺寺藏。
島田隨即考量的是“逸品畫風”牽涉到的繪畫種類。在中唐時期,逸品畫風起自山水畫,“潑墨”即是畫山水的手法,但到唐末五代時期轉向人物畫。傳至米芾(1051—1107),南宋趙希鵠(1170—1242)《洞天清錄》“古畫辯”載:“米南宮多遊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仿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為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作一筆。”島田認為,現存山水中的絕佳好例,是傳南宋牧溪的《瀟湘八景》(圖6)。另宋初金陵的徐熙,是花鳥畫在“逸品畫風”的代表人物(圖7),這一觀點可能來自《圖畫見聞志》卷一“論黃徐體異”:“黃家富貴,徐熙野逸。”

圖6 南宋,牧溪,《瀟湘八景·遠浦歸帆》,軸,紙本墨筆,32.3 x 103.6釐米,日本文化廳藏。

圖7 傳五代,徐熙,《雪竹圖》,軸,絹本墨筆,149.1X99.1釐米,上海博物館藏。
島田認為,北宋神宗時期,是繪畫跳上新發展階段的轉機,畫院的畫風為之一變,以文人畫觀主張的繪畫擔任了主流。所謂文人畫觀,在他看來,是“以一種內在立場來觀照表現作用的主體和作品。文人畫觀要求畫面清淨潔致,不再接受奔放又露骨的粗筆。與文人畫幾乎無法相容的禪僧墨戲則繼承了最初的“逸品畫風”,這也是牧溪被湯垕評為“麄惡無比”的原因。而梁楷之作,亦即在簡略描寫的恣意粗筆之上,賦予了深刻的寫實基礎,則被島田看作是統一“逸品畫風”和精細寫實之風的作品。事實上,在此的討論略為粗疏,以至於沒有注意到至少在文人畫的早期階段,存在與“逸品畫風”的內在聯繫。
在論文的最後,島田作出結論,“逸品畫風”從廣泛的意義上而言,可以認為是每一時代在正統畫風之外尋求新的創意,恰如旋轉中與向心力抗衡的離心力,因此在不同的時代,它呈現出種種不同的面貌。如晚明浙派中的“狂逸”(圖8)、以及從明末而始的朱耷、石濤以至高鳳翰、李鱓等派別。但後世發展出的“逸品畫風”,與中唐時初興而起的“逸品畫風”相比,它們的重要意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換言之,最初的“逸品畫風”對後世的影響最為重大。另外,島田所考慮的“逸品畫風”主要還是從形式出發,他所舉的後期畫家,大致也都具備“簡略”和“粗筆”兩種特徵,只是表現的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圖8 明代,張路,《蒼鷹逐兔圖》,軸,絹本設色,158X97釐米,南京博物院藏。
二、《逸品畫風》觀點的西方延續
《逸品畫風》一文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西方人得以理解“逸品”,是因為島田提到了其與禪畫之間的關聯,而這些保存於日本的禪畫,正是西方較早接觸到的中國畫。如喜龍仁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繪畫:代表性大師與原則》中,就將南宋牧溪的禪畫作為“逸品畫”看待。而在中國古代畫論中其實並沒有直接的依據。《逸品畫風》譯入美國之後,在1970年波士頓美術館出版的重要圖錄《禪宗的繪畫與書法》中,撰寫者同樣提到,“逸品”一般採用水墨畫,筆墨粗獷、不遵從“骨法用筆”,五代的貫休被看作是第一個採用“逸品”風格的禪畫家。1982年,迪特里希·澤克爾(Dietrich Seckel)在《禪宗藝術》一文中,則將梁楷的《六祖斫竹圖》看作“逸品”的典型(圖9),認為禪畫在所有傳統畫風中,選中了唐和五代興起的“逸品畫風”。這些觀點實際上都沒有脫離島田對“逸品”的描述,以及對這一風格範疇內畫家的列舉。

圖9 南宋,梁楷,《六祖斫竹圖》,紙本墨筆,軸,73x31.8釐米,東京國立博物院藏。
另外,島田認為唐代的“逸品畫風”在北宋神宗時代被文人畫觀之作所取代的觀點,也被西方學界所接受。如哈佛大學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員卜壽珊(Susan Bush)等在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初版於1985年《早期中國畫論》中(圖10),即提到了李嗣真所論的“逸品”(Untrammeled Class或i-pin)。在她看來,逸的範疇(i category)最初是一種無法被歸類的才華的群體,這種分類法得到了朱景玄和張彥遠的迴應,並影響了後世。在張懷瓘的《唐朝名畫錄》中將“逸品”單列,三位畫家“拒絕正統”,為許多唐代之後的畫論提供了樣板。唐代以後的畫家對過往發展出歷史的視角並採用不同的途徑來為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分類。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中仍然採用了神、妙、能分類,但將“逸格”放在三類之前,而非其後,意味著“不受規則限制的畫聖”(Sage of Painting outside the rules)。後世“逸品”的地位衰落了,這種分類的方式也被其他的構建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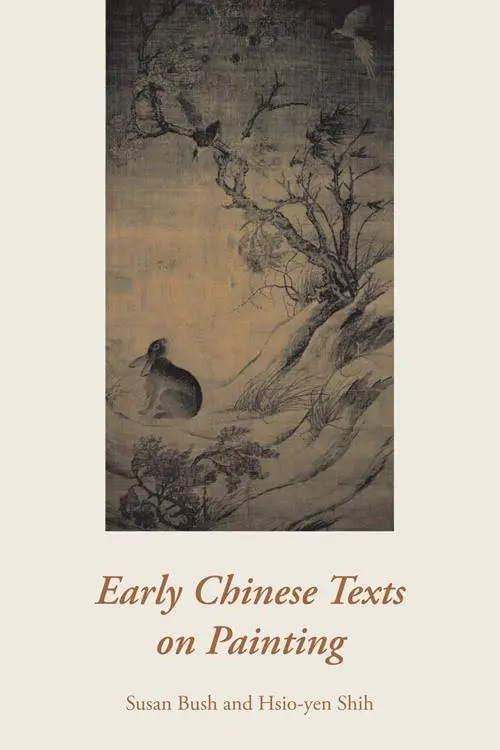
圖10卜壽珊(Susan Bush)的《早期中國畫論》
繼美國學者李雪曼(Sherman E.Lee,1918—2008)在1962的《遠東藝術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中,將禪畫歸於“天然風格”(Spontaneous Style)之後,《逸品畫風》的英文譯者高居翰曾撰寫《中國繪畫史三題》,其中包括《中國繪畫的率意與天然:一種理想的興衰》一節,主要的觀點幾乎全由島田論文而生髮。在文中,高居翰將“率意”(quickness)與“天然”(spontaneity)指向畫論中的“逸品”,事實上這兩個稱謂源自島田所論的“粗筆”與“簡略”。在高居翰看來,在北宋的蘇軾時代,即出現了一種新觀念:文人畫家獨享率意與天然的理想,即佔領了“逸品”之地位,他們貶低職業畫家的策略之一就是將其置於趣味繁瑣枯燥的一端。這一觀點也來自島田文中提到的神宗時代文人畫觀導致“逸品畫風”式微的認識。
與島田一樣,高居翰認為,在南宋時期,“逸品畫風”一度走向了禪畫的領域,影響了禪師和服務於其他領域的畫家。在12世紀晚期和13、14世紀,禪畫家採用“率意”與“天然”的畫風,創作了一些極其簡潔明晰的圖像。高居翰讚賞廣泛意義上的禪畫,也包括詩意畫,如《瀟湘八景圖》等,並將其作為“逸品畫風”的傳承者。同時他看到,文人畫評並不接受這類“逸品畫風”的特質。對文人畫家而言,“率意”與“天然”的理想必須用規則的筆法來調和,不容許脫離常規的真正自由。高居翰並不承認在後世畫論中一再出現的倪瓚(1301—1374)的“逸品”與唐代“逸品畫風”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聯繫,因為倪瓚的絕大多數畫作似乎是在相對嚴格的控制下構思完成的。元代的還原早期“逸品”的畫者,在他看來是擅長墨法的方從義(1302—1393)。(圖11)另一個“率意”與“天然”畫家出現的時期,則是明代晚期,畫家包括吳偉(1459—1508)、唐寅(1470—1524)和徐渭(1521—1593)。但當時的畫論家,如李日華(1565—1635)、謝肇淛(1567—1624)、詹景鳳(1532—1602)和張醜(1577—1643)皆傾向於認為這一時期已不應實行“率意”與“天然”的畫風。明亡之後,這一路畫家又出現了石濤(1642—約1707)及揚州畫派諸人等。但最終,高居翰認為:“率意和天然模式起初具有超越規則的重要意義,卻以成為對法則、創造和藝術表現力的失敗作出補償的一種常規方法而告終。” 在後記《寫意:中國晚期繪畫衰落的原因之一》,高居翰又提出,“率意”與“天然”的創作模式使晚期畫家匆忙完成過多的作品,但每一幅都思考不足,用心不夠。因此“率意”和“天然”模式起初具有超越規則的重要意義,卻以成為對法則、創造和藝術表現力作出補償的一種常規方法而告終。

圖11 元代,方從義,《雲山圖》(局部),卷,紙本水墨,26.4 × 144.8 釐米,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篇論文在島田的基礎上進一步試圖解決“逸品畫風”在畫史脈絡中走向的問題。文人畫觀對“逸品”的佔領導致南宋禪畫等類型的畫作沒有受到肯定,晚期的類似畫風又僅僅繼承了“粗筆”和“簡略”的表面樣貌,卻失去了早期的獨創和活力。換言之,高居翰以“逸品”這一畫史名謂的內涵變遷,試圖指出晚期中國畫史中部分“逸筆”之作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特點,在此畫史和“逸品畫風”共同走向了衰落。
二、亞歷山大·索珀《石恪與逸品》中的再度論述
繼島田之後,布林茅爾學院的藝術史教授,亞歷山大·索珀(Alexander C. Soper,1904—1993)於《亞洲藝術檔案》發表了論文《石恪與逸品》。《石恪與逸品》一文主要研究了日本正法寺所藏的五代畫家石恪名下的《二祖調心圖》。這是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兩個對軸,從風格來看很接近牧溪、梁楷一類的粗筆禪畫人物。索珀就這件畫作提出了幾個疑問。首先,關於畫的題名《二祖調心圖》,究竟是表現兩位禪宗祖師還是禪宗二祖慧可,他認為兩種畫題似乎都能成立。第二是鈐印的真偽,該畫中有南唐“建業文房之印”、北宋哲宗時代出土的鳥蟲書印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徽宗的“宣和”“政和”連珠印、南宋高宗的“德壽殿寶”等,但這些印被證明都不可靠。根據索珀的推測,這件作品的年代在於宋末元初,甚至更晚。

圖12亞歷山大·索珀正由弗利爾美術館的總監米洛·C. 比奇授予查爾斯·朗·弗利爾獎章,1990年。
除了《二祖調心圖》畫作本身的內容和真偽之外,索珀還進一步討論了石恪的作品風格究竟為何。索珀談到,當下的學者普遍認為,《二祖調心圖》沒有忠實地表現十世紀晚期文獻所載的石恪的風格。因為大多數載錄都沒有體現出石恪擅長創作禪畫主題,相反,從文獻來看,石恪反而是個復古主義者,如《益州名畫錄》中“攻古體人物”,《聖朝名畫評》中“宗吳道子之畫”,《宣和畫譜》“好畫古僻人物”等。除此之外,在北宋人的載錄中,石恪還擅長作帶有滑稽意味的畫題。如北宋李廌(1059—1109)《德隅堂畫品》載石恪所畫《玉皇朝會圖》:“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時出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作形相或醜怪奇倔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系魚蟹於腰以悔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媼嘗醋圖,蹇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妻對案置酒,主供帳果餚及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蟹,欲調後人之笑耳。”類似的畫題,筆者認為可能頗接近南宋帶有滑稽視感的雜劇冊頁,如《眼藥酸》《大儺圖》等。(圖13,14)除此之外,索珀從蘇軾所撰的《石恪畫維摩頌》推斷,石恪可能很擅長畫如唐代敦煌壁畫中的盛大而繁密的構圖。

圖13 南宋,佚名,《眼藥酸》,冊頁,絹本設色,23.8x24.5釐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4南宋,佚名,《大儺圖》,軸,絹本設色,67.4x59.2釐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索珀指出,關於《二祖調心圖》對軸中顯示的畫風,大致出現在較晚的文獻對石恪的載錄中。《畫鑑》載:“石恪戲筆畫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麄筆成之。”然而北宋李廌在《德隅堂畫品》中,載石恪“故畫筆豪放,時出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作形相或醜怪奇倔以示變。”似乎重點論述的是醜怪奇倔這一特點。索珀由此認為,湯垕所見到的未必是石恪的真跡。另《洞天清錄》“古畫辯”載:“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索珀特別指出“勁利”一詞,應譯為“forceful and keen”,這很接近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卷六中對陸探微(不詳—約485)的描述:“筆跡勁利,如錐刀焉。” 與湯垕所描繪的“麄筆”不符。
此外,就“簡略”而言,索珀考慮的是,孫位和李靈省可能都將遠景中不重要的物象進行了簡化,如《唐朝名畫錄》載李靈省“若畫山水、竹樹,皆一點一抹便得其象,物勢皆出自然。或為峰岑雲際,或為島嶼江邊,得非常之體,符造化之功。”因此,孫位可能採用了“光學現實主義”(optical realism),正如希臘化時期(Hellenistic period)的某些藝術家放棄了全景的描繪,取而代之印象主義(impressionistic)的片、點和潦草的色彩。而這一試驗後來成為北宋後期的普遍畫法,如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所撰寫的:“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也。” 最後,《德隅堂畫品》中載孫位曾作《春龍起蟄圖》,“窮究百物情狀”,和索珀所認為的石恪畫大場面作品的分析有類似之處。因此,《益州名畫錄》中的“逸品”實際上已經與唐代有所不同,由“粗筆”和“簡化”變化為“筆精、簡化和宏大場面”。
由此,索珀在島田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出,石恪的風格更接近黃休復所舉的孫位。石恪之所以被稱為“逸品”在於其滑稽的主題,而非他的粗筆畫法。《圖畫見聞志》中載其“筆墨縱逸,不專規矩”等,正體現了他有能力遵守法則。更進一步說,石恪的畫風可視為“紀念碑樣式”(monumentality)和“嘲弄”(mockery)的結合,但《二祖調心圖》卻與宋元時代的成熟禪畫風格類似。因此,雖然島田認為《二祖調心圖》是石恪之作的模本,製作時代不會早於元代;但索珀卻認為《二祖調心圖》實際上與石恪並無關聯。真正能夠反映石恪面貌的,應是大德寺《五百羅漢圖》中《火熨斗》一圖的下方,兩個滑稽人物和小鬼一起模仿徽宗《搗練圖》的詼諧感(圖14)。

圖14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周季常,《五百羅漢圖》之《火熨斗》(局部),112.5x53.2cm,軸,絹本設色,大德寺藏。
索珀這篇論文雖然否定了部分島田的觀點,其實是在《逸品畫風》的基礎上所撰寫的。他認為石恪在最初的載錄中,應是具有幽默風格的道釋人物畫家,而非唐代“逸品”範疇內的粗筆狂醉畫風。而《二祖調心圖》與後世的禪畫殊途同歸,可以定為宋元或更晚期的作品,且與石恪無涉。這篇論文的意義還在於,作者試圖釐清在唐宋“逸品”變遷的時期,蜀地的“逸品”觀感究竟為何的問題。在島田的理解中,唐代“逸品畫風”與後世的禪畫是相互傳承的關係,索珀實際上並不否認這一點,但他作了更深入的探討,認為在“逸品畫風”被文人畫觀影響之前,還存在一個階段,即“筆精”,帶有“光學現實主義風格”,可能表現宏大,或滑稽場面的蜀地繪畫。
另一方面,索珀對石恪的筆墨的研究還嫌不夠深入,事實上石恪並非不可能兼有“粗筆”和“筆精”之風。如《聖朝名畫評》載:“喜作詭怪而自擅逸筆”,《宣和畫譜》載:“益縱逸不守繩墨”,《圖畫見聞志》載:“筆墨縱逸”等,再如《畫繼》:“畫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為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陸游(1125—1210)《遊三井觀》中提到:“石恪雖少怪,用筆亦跌宕。”都顯示出石恪的用筆有不守繩墨之風。這些文本與《畫鑑》中載“戲筆畫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麄筆成之”可能存在著傳承關係。畫史中的石恪形象,是否存在兩種不同的風格並存的可能,索珀並未能就此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三、倪肅珊的《晚期畫論中的逸品》之續篇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亞系的教授倪肅珊(Susan E. Nelson)的論文《晚期畫論中的逸品》, 意在為《逸品畫風》作續篇。該文收錄於198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出版的《中國藝術理論》一書中,該書是二戰後西方研究中國藝術理論的重要文集。
在論文的開端,倪肅珊指出,黃休復雖然認為孫位是“逸品”畫家,但在《畫繼》中,孫位並沒有得到讚賞。從這時起,畫史中出現了新的文人畫觀運動,這一觀點與島田基本一致,作者隨即以四個部分來論述晚期“逸品”的生成這一問題。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引用明清時代的畫論文本,論證在晚期的“逸品”範疇中,有一個由兩位畫家組成的核心,就是宋代的米芾和元代的倪瓚,另元代高克恭(1248—1310)作為“米法”的傑出仿效者(圖15),也被董其昌列入“逸品”畫家的範疇,這類觀點主要出自董其昌。但卻受到了謝肇淛(1567—1624)的反對:“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仿,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事實上,謝在這段話之前還言道:“至王洽始為潑墨,項容始尚枯硬。”實際上是將米芾和倪瓚(圖16)分別視為王洽(即王墨)和項容等唐代逸品畫家的不合格的繼承者。而倪肅珊認為,在整個明清時代,米芾和倪瓚都被相提並論,認為是唐代之後的兩位“逸品”大師,他們分別代表了墨和筆的傳統。

圖15 元代,高克恭,雲橫秀嶺圖,軸,紙本設色,182.3x106.7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元代,倪瓚,《六君子圖》,軸,紙本墨筆,61.9x33.3cm,上海博物館藏。
在該文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到了後世摹仿米芾和倪瓚的現象。黃休覆在《益州名畫錄》中言道:“畫之逸格,最難其儔。”可見逸格在唐代之後就有“不可學”(inimitable)之義。倪肅珊認為,就米芾和倪瓚而言,“不可學”有兩個含義,首先是內在的複雜涵義微妙,難以模仿;第二是畫家個人的氣質不能習得。但在倪肅珊看來,倪瓚實際上是個勤奮的畫家,他的風格並非是不可學習的。
在第三部分中,倪肅珊提到,畫評雖然強調後期的逸品大師是不可模仿的,但部分模仿者也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如在宋代時,由於馬和之(活動於12世紀)和趙令穰(生卒年不詳)的風格接近米法,因此他們與元代高克恭、方從義,甚至曹知白(1272—1355)一樣,被晚期畫論家視為“不可學”的逸品畫家。再如清代沈宗騫(1736—1820)在《芥舟學畫編》卷一“神韻”中雲:“且如米元章、倪雲林、方方壺諸人,其所傳之跡,皆不過平平之景。而其清和宕逸之趣,飄渺靈變之機,後人縱竭心力以擬之,鮮有合者。”可見這些模仿者由於學習了“逸品畫風”,同樣獲得了“不可學”的評價。
在第四部分中,作者總結了宋之前與晚期“逸品”之間的差別。她認為唐代的“逸品”畫家更為特立獨行和帶有實驗的性質,但晚期的“逸品”畫家則顯示出疏離、平淡和冷漠的特質,畫作也更為自抑,實際上走向瞭如唐代那般自由創作的反面。倪肅珊將唐代的“逸品”譯為“untrammeled”,意為從外在束縛中解脫;而認為元代後期(post-Yuan)的“逸品”應直接翻譯為“i”,意為淡然而不受外在束縛的影響,換言之,也就是閒散之“逸”(“relaxed” i)。因此從本質上而言,“逸品”含義的變遷,應歸於文人畫對“自由”的重新闡釋和吸納。在倪肅珊看來,處於“逸品”涵義變革的轉折點上的畫家是米芾,他調和了兩種畫風,既有對唐代的繼承,又有平淡的文人風格。
最後,作者提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文人畫的出現實際標誌著唐代“逸品”的沒落,他們將後者粗野和率性的畫風變得高尚文雅。而早期“逸品”畫之殘餘不再受到人們的尊敬,它的繼承者僅有南宋的禪畫家和明代的一些狂怪畫家。總之,倪文致力於解答的是晚期“逸品”如何在文人畫範疇中發展和變遷,並認為米芾是“逸品”進入文人畫範疇的過渡人物,她為島田之文作續篇之意是頗為明顯的。
四、“逸品”與詩意的關聯
島田修二郎、亞歷山大·索珀和倪肅珊的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側重點,但在某一基本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致的。亦即,唐代的“逸品畫風”並沒有作為中國畫的主流風格延續下來,它的某些特徵以另一種方式顯現,如島田和倪肅珊所論的禪畫和“狂逸”畫風,索珀所論的“光學現實主義”(optical realism)等。在這之後,另一些學者,如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等則進一步論述了“逸品”在17世紀日本的涵義,並在這一基礎上作中日繪畫的比較。
徐小虎在經由1979年和1980年發表的三篇對早期南畫的研究整理而成的著作《南畫的形成:中國文人畫東傳日本初期研究》中,對日本的“逸品”理解作了充分的闡述。她首先引述了島田的觀點,即認為“逸品畫風”置“骨法用筆”於不顧,在象形上沒有明確的輪廓,然而卻將自然形態施以顯著的變化與簡略化。在徐小虎看來,線條至高無上的地位在14世紀的中國牢牢地建立了起來,非線性、加強渲染模式的試驗漸漸被視為非正統的。而這一現象的種子在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已經播下,即“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之說。
徐小虎接著提到,與逸品畫風密切相關的“潑墨法”,或與之相近的“破墨法”,因為其更直接,更自由的做法,在德川時代的理論家和藝術家心目中則佔有很高的地位。正如《逸品畫風》一文最後的觀點,正統畫風宛如一條所有事物旋轉的中軸線,逸品畫風則是離心力作用下的產物。徐小虎發現,德川時期的日本畫家和畫論家知道,逸品的觀念從唐代就出現,到了北宋和元代則與理想主義者——即士大夫或文人的傳統深深結合在了一起。但在日本,這種風格與牧溪和玉澗聯繫到了一起,並於15至18世紀間發展成高度的藝術。與之同時,在中國的明清文獻中,“逸品”則意味著一種品質的等級,已經失去了明確的技術相關性了。
藉此,徐小虎將北宋以後“逸品畫風”的發展,分為“非線性”和“線性”兩種方式。“非線性”即為潑墨風格,也可理解為無皴法,且帶有簡化意味的風格。在此,她舉出的藝術史實例,包括藏於弗利爾美術館的傳米芾的《雲起樓圖》(圖17),傳蘇軾的《枯木竹石圖》,被沈括形容為“用筆草草,近視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淡墨輕嵐為一體”的蕫源和巨然之作;另有《畫史》載錄的米芾作畫採用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米芾讚賞李成畫松樹“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她認為這些士人將“寫意”作為對“真”或“理”的追求。除了禪畫家之外,日本人確實將“逸品”進一步與蕫源聯繫起來。18世紀的日本畫論家桑山玉洲(1746—1799)曾在《玉洲畫趣》中言道:“可稱草畫之趣者,只在寫意之法,或如王洽之潑墨法、米法、蕫法之類。” 這一點與倪肅珊所論的中國晚期畫評中,僅僅將米芾和倪瓚視為“逸品”畫家並不一致,很明顯,日本方面將“逸品”的範疇限於“墨法”的範疇,還加入了畫史中擅長“墨法”的蕫源。而“線性”風格則與之相反,是中國元代以後發展出的文人畫中帶有筆法的“逸品”之作。

圖17傳北宋,米芾,《雲起樓圖》,軸,絹本墨筆,50 x 78.8釐米,弗利爾美術館藏。
在徐小虎看來,到了元代,趙孟頫是排除了“逸品”技法的畫家,他以後的文人畫變得越來越注重筆墨肌理,導致17世紀時產生疏與密兩類幹筆線性風格,而“逸品”一詞被侷限在品質感上,即最上等的理想主義者繪畫。然而,玉澗(若芬)減筆渲染風格在16世紀日本日漸上升的聲勢,證明了一種長久以來與“逸品”相關聯的傾向無筆、潮溼和簡略意象的癖好。在18世紀的日本,“逸品”很少指線性風格,而是保持了粗率的、減筆的、潮溼的,與唐代大師王洽、王維、蕫源、二米聯結的一種抒情描繪。可見中日的“逸品”觀已經分道揚鑣,中國重“筆意”,“無筆”被視為奇、怪、瘋;日本還是聯結到牧溪、玉澗風格的潤溼、無定形與非線性作品;中國發展出了文人畫的“筆法”,日本則發展出了以渲染為基礎的非線形方法,稱為「垂し込み」,此種技法表達了一種“詩意的喚起”。
由此可見,徐小虎對“逸品畫風”的理解實質上又進了一步,體現為除了將“逸品”與後來的禪畫聯繫在一起之外,她通過對日本畫的研究,認為唐代“逸品”的發展走向的不僅是禪畫的水墨風格,還有詩意的喚起感。在日本人的感知中,水墨與自由多變的形式、情感充盈的意象和表現密切相關,而這類形式的重要性在中國人的感知中是相對次要的。因此日本禪畫藉著改變中國範例畫的表現語彙和方法,慢慢地轉化為一種更加詩意、本土傾向的表達形式。如在室町時代的詩畫軸中,畫僧天章周文(約活動於1423—1458)繼承了源自夏圭傳統的元、明繪畫之堅實物象,以及將封閉空間轉化為幾乎透明的感性形式(圖18),使之靈動流暢,充滿引人遐思的空茫氣氛。可見南宋畫在此也被認為是詩意喚起的。而日本人所理解的“文人畫”,實際是由室町時代開始,將減筆水墨渲染風格與草書及“寫意”聯繫在一起的日本禪僧之作,是學習中國禪畫和南宋院畫的融合。

圖18 日本,室町時代,1447,天章周文,《竹齋讀書圖》(局部),紙本墨畫淡彩,136.6x33.6cm,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國寶。
徐小虎還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桑山玉洲在《繪事鄙言》中,將“逸格”解釋為“尋常畫法脫略化的清奇幽妙之格”,將唐代的王洽與張志和、宋代的米芾父子、元代的黃公望、倪瓚、高克恭視為“逸品畫家”,事實上他的認知來自中國渡日畫家伊海(生卒年不詳)和池大雅(1723—1767)的模仿之作,並結合了中國文本的介紹想象而成。因此徐小虎認為18世紀的日本藝術家和理論家所瞭解的“逸品”事實上仍是島田所論的“粗筆”和“簡略”的延續。但這種延續所造成的結果,包括將“逸品畫風”的變遷與“詩意畫”這一較難作出界定的畫史概念聯繫在一起。
關於“詩意畫”最廣為人知的著作是高居翰的《詩之旅》,該書脫胎於1993年4月在哈佛大學做的賴世和系列講座,開章便作了敘事畫和詩意畫的區別界定。在高居翰看來,敘事畫如敘事文一樣,能在一定篇幅中敘述廣泛的內容,描述一個較完整的事件或意象,如《閘口盤車圖》和《清明上河圖》。相對而言,詩意畫如同詩歌,能把人帶出日常生活處境,能夠以簡單的形象喚起深刻而強烈的情感。高居翰在此所論的“簡單形象”,筆者以為指的是不具有特定細節和意義的,可以承載抒情體驗的形象,正如高居翰所言的“普通常見的內容”。另一方面,與島田所論的“簡略化的自然形態”在意義上有相近之處。
就詩意畫的範疇而言,高居翰確實是反筆墨的。但這不完全因為他不瞭解中國傳統繪畫之美,而是因為高居翰認為筆法的程式化,在山水畫中犧牲了“區分土石的質地、天空陰晴變化的視覺差異,以及表現光和空氣的瞬間效果、季節與晝夜的變化等等的技法”。雖然高並沒有具體陳述詩意畫的組成要素,但可以看到,首先是可以承載抒情體驗的畫面形象,第二是環境氛圍的喚起感。高居翰認為,最好的詩意畫依賴於完全掌握了某種再現的技巧,以看似輕鬆的方式,來表現空間、氣氛、光亮以及物象表面的細微和轉瞬即逝的效果。
究竟如何才能表現出此種效果,高居翰並沒有從技法的角度作出專門的論述,但石慢(Peter C. Sturman)在書評中指出,所謂抒情的表達,是以職業畫家融入其光學經驗(optical experience)來呈現的。從高居翰所舉的例子來看,首先是部分南宋的院體畫,包括傳為南宋馬遠、梁楷、夏圭等畫家(生卒年均不詳)的作品;隨即越過元代,來到晚明的蘇州,將張宏(1577—1652後)、李士達(活動於1574—1620前後)和盛茂燁(活動於17世紀)的畫作看作是詩意畫的典型(圖19),與石慢的論述基本符合。而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詩意畫,如池大雅、與謝蕪村(1716—1783)等也都延續了這路畫風。正如《繪事鄙言》中所言,伊海和池大雅都被認為是當代的“逸格”畫家。

圖19 明代,盛茂燁,《平沙落雁》,盛茂燁、陳煥、沈明臣、李士達、沈宣,《瀟湘八景圖冊》,八對開冊頁,紙本水墨設色,24X25.2釐米,弗利爾美術館藏。
當然,西方學者的類似理解,也並非完全孤立地從東亞語境出發。首先,在西方藝術史中,詩意的繪畫被認為出自18到19世紀歸為浪漫主義的一些畫家,如約翰·康斯泰布爾(John Constable,1776—1837)、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法國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的讓·巴普蒂斯特·卡密耶·柯羅(Jean-Baptise-Camille Corot, 1796—1875)等。康斯泰布爾善於捕捉自然界瞬息變幻的特性——雲、光和空氣。他曾以天空為題畫了無數習作,因為它是“基調、標準和抒發情感的主要工具。” 柯羅充滿光線變幻的繪畫被稱為“抒情風景畫”。(the lyrical landscape)。第二,西方19世紀30年代以來興起的先驗主義運動,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愛默生的《自然》(Nature,1836)和亨利·大衛·梭羅的《瓦爾登湖》(Walden,1852),表現了心靈與自然的統一,而風景畫是將這種統一表現為視覺的途徑。在西方藝術史傳統中,自然、氣候和光線的變化,體現了詩意的情感、懷舊的鄉愁和神創的自然。正如大英博物館的勞倫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在其初版於1908年的《遠東繪畫:以中國和日本的圖像藝術為主的亞洲藝術導論》中,將牧溪的《煙寺晚鐘》(圖20)與19世紀法國畫家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的《晚禱》聯繫在一起,認為是飽含詩情的創作。

圖20 南宋,牧溪,《煙寺晚鐘》,軸,紙本水墨,33x104釐米,畠山紀念館藏。
由此可見,高居翰等學者的中國“詩意畫”理解,除了受西方詩意風景畫傳統的影響,也是在日本延續中國“逸品”繪畫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正因為他們站在整個東亞範疇上看待“逸品”的發展,最終將“潑墨”與“墨法”聯繫,將“粗筆”“簡略”與“簡略的形態”聯繫,而水墨氤氳與畫中空間、氣候、光亮和質感的關係,又被認為是詩意畫中最重要的要素,這與中國慣常理解中的“詩畫合一”是有所不同的。
五、結語
本文關注的是西方學者對“逸品”的理解,整體而言,這些研究觀點有相互補充和層層遞進的作用,與中國學者的理解相比也有其獨特之處。首先,西方的理解主要受島田修二郎《逸品畫風》的影響,主要從繪畫技法方面理解“逸品”,認為唐代的“逸品”畫包括“簡略”和“粗筆”兩種特徵,南宋的禪畫和晚明的“狂怪”畫風延續了最初的“逸品畫風”。第二,大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唐代和明清時期對“逸品畫風”的理解之間存在脫離的現象,這種脫離主要發生在北宋晚期文人畫興起之後,早期的“逸品”是獨特的畫作,晚期的“逸品”則是對米芾、倪瓚等文人畫的讚賞。第三,在索珀看來,“逸品”的轉型在蜀地就發生了,在倪肅珊看來,這種轉型在宋元時代,而轉型的根本變化是從重“墨法”到重“筆法”。第四,中國的詩意畫至少自唐代開始即有之,但高居翰等卻認為主要出自南宋和晚明,這兩個時期的詩意畫都對日本有較深的影響,也與島田“逸品畫風”的後期延續觀點不謀而合。
最後筆者要指出這些研究者們的一點疏忽,那就是他們都跟隨島田的觀點,認為北宋的文人畫觀使唐代“逸品”逐漸淡出畫壇的主流。事實上,北宋的文人畫恰恰與王墨等唐代“逸品”畫家是有所關聯的。《夢溪筆談》中載錄宋迪(活動於11世紀)的《瀟湘八景圖》,“汝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畫繼》中又載北宋畫家陳用之(生卒年不詳):“張絹素倚之牆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丘,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類似的創作方法與風格,與前文所載的《唐朝名畫錄》中“(王墨)隨其形狀,為山為石,為云為水。”“(李靈省)皆一點一抹,便得其象”的載錄非常類似。再如《洞天清錄》“古畫辯”中形容李公麟:“伯時惟作水墨畫,不設色。其畫殆無滯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偽作。其餘人面相尤妙。”又言道:“李伯時有逸筆。”可見北宋文人畫的技法中可能仍含有唐代“逸品畫風”的餘韻,而這段藝術史的歷程卻很少為學者們所關注。
(本文原標題為《西方視野中的多重“逸品畫風”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原載於《美術》2020年第8期。原文有註釋,此處限於篇幅未予收錄。)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西方視野中的多重“逸品畫風”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