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有的,必體現在行動上。對於作家,必體現於筆下
◆真正的現實主義,不但要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還要寫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只寫深了前一點,固然會是好作品。同時可信地寫到後一點,則會好上加好。而只要寫到後一點,則溫度在焉

▌樑曉聲,1949年生於哈爾濱,作家、學者,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人世間》等作品數十部,《人世間》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楊樂 攝影)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程青
熱血,真摯,關注社會,樑曉聲的小說總是與時代和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他的寫作注重把社會重大命題納入到個人經驗之中,將現實主義傳統發揚光大,並重申了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上世紀80年代初他的作品便風靡全國,由他那些讀者眾多的知青題材小說如《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等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觸動人心,那時他便是家喻戶曉的作家。時隔三十多年他推出三卷本長篇小說《人世間》,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經歷折射出近半個世紀家國、制度、情感結構、道德倫理的嬗變,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這部九十多萬字的具有史詩性的長篇鉅製,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繼《平凡的世界》後又一部樸素、真誠、飽含悲憫之心的作品,並獲得代表中國長篇小說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學獎。
這樣成功的一位作家卻說:“我已難達預想之地——從頭來過或許可能。但我的眼一直望向它,努力過了,接近了一步,算是欣慰吧。”如此肺腑之言,令人對文學與人生更添敬愛和思考。
《瞭望》:你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等作品很早即風靡全國。這些作品一開始就貼近時代,關注社會,你是怎麼找到這樣一種文學表達的?
樑曉聲:也可以這樣說,貼近時代,關注社會,呈現弱勢人物及群體之命運,是中國那一時期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的文學理念。這也幾乎必然,因為所汲取的幾乎是同樣的文學營養。所謂知青,那時已淪為弱勢群體,牽動千千萬萬家庭的親情神經。我曾是兵團知青,寫我和寫他們交織為寫我們。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約稿,要求寫北大荒知青,當時也只不過寫了一個傳奇和悲劇色彩兼具的浪漫故事。發表後,許多知青覺得被代言了。這觸動了我,遂自認為有代言的義務。
《今夜有暴風雪》和《雪城》,確乎是代言意識支配下的產物。至於《知青》《返城年代》,則已擺脫代言意識,主要想表現特殊年代大背景下,人應該恪守些什麼。
《瞭望》:你19歲到生產建設兵團,兵團的生活經歷給了你怎樣的影響?這段艱苦的生活是否對你的創作有助益?
樑曉聲:兵團知青與插隊知青雖都是知青,生活狀況卻甚為不同。兵團知青有工資。我所在的一師一團,屬寒帶地區,有9元的寒帶補貼,故我們的工資是41元多。下鄉後,連隊就是單位,戰友就是同事,團、師就是上級主管部門。等於踏入了社會。回首往事,我從不認為艱苦多麼值得說道,既不是長徵也不是修青藏公路,更不是抗聯戰士,不值得說太多。但也畢竟艱苦,而過一段艱苦生活,對人不完全是不幸。但我畢竟是文學青年,無書可讀有精神飢渴感。與那個時代的總體氛圍格格不入,甚至牴觸,也令我有思想苦悶。
幸運的是——當年瀋陽軍區極其重視兵團知青的文藝生活。兵團總司令部每年舉辦各文藝類別的學習班、提高班。一名知青,只要有公認的文藝特長,那就必定受到關注,獲得參加機會。即使出身不紅,往往也會破例。我有幸參加了多次小說創作學習班,結識了全兵團當時的幾位優秀的文學知青。與他們在一起討論文學,交流創作體會,使我受益匪淺。
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不但促進了我的創作,給予了我獨特的素材,也為我日後的人生拐點預鋪了一段路面。
《瞭望》:最初是什麼契機促使你走上文學道路?
樑曉聲:緣由如下:一是具有以想象和思考為享受的潛質,想象的潛質尤為重要。兩種愉快我都享受。我的童書閱讀經歷幾乎為零。小時候母親講給我們聽的也大抵是成人故事。我從小學四年級就接觸成人文學了,起初是小人書,後來是成人小說。二是有文學環境,底層人家當然沒有那一環境,但長我6歲的哥哥是文學發燒友,所以我不缺書看。家裡連收音機都沒有,讀文學名著不啻於精神留戀於嘉年華。三是勤於寫作訓練。參加兵團文學創作學習班,成為復旦大學創作專業的學生,畢業後分配在與文學關係密切的北京電影製片廠——以上外因不斷激發內因,想不勤奮都做不到。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沒形成什麼成熟的文學理念,只不過明白一點——作家是時代的文學書記員,反映種種他者的命運給更多的人看。
《瞭望》:你的作品樸素、真摯,飽含悲憫之心,你是如何做到不僅使小說中的人物富有時代意義,而且還帶著煙火氣和雕塑感的?
樑曉聲:這是一個較專業的問題。首先受益於好的文學作品的薰陶。這類作品的首義是人文元素,包含了你說的悲憫情懷。而這不是方法,是自己的心被感化在先的結果。好的文學作品必有好的情節,好情節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自會帶有煙火氣;必有好的細節,好細節有利於人物的生動。至於雕塑感,則是電影對我的正面影響。我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和兒童電影製片廠各工作了十幾年——我寫人物,在某些片斷上,總是會自問:如果在銀幕上,這一片斷該怎樣?你說的雕塑感,其實也是畫面感。
《瞭望》:你的寫作始終帶著溫度,滿懷對社會和他人的關切,是否與你個人的成長背景有關?
樑曉聲:簡直可以說,溫暖社會,軟化人心,是文學有史以來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學大抵具有這種品質。但文學是多種多樣的,好文學也是各不相同。《阿Q正傳》並無溫度,《死魂靈》也沒有,然而都是經典。我青年時受西方啟蒙文學影響甚深,它們大抵是有溫度和對社會對他人的關切,我的文學營養如此,所以後來形成的理念如此。
世界改變了很多,文學也是。但有些東西一直未變,不論對文學還是對世界。並且,所幸未變。底層人間的一個真相是——因其為底層,所以更怕人心之冷。人們需要抱團取暖,否則生活更加艱難。鄉裡鄉親、遠親不如近鄰、發小關係,都是溫度的概括。
我與底層關係密切,是經常感受著那種溫度成長的。當然,父母的善良,每每給我直接影響。特別是母親,她的善良也體現於對一切小動物的愛護。並且,溫度還體現於鄰居他人對我家、對我的無私幫助。二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感激》,也是對民間溫度的記錄。內心有的,必體現在行動上。對於作家,必體現於筆下。
《瞭望》:你是在什麼情形下決定寫《人世間》的?聽說你是在稿紙上書寫的,寫作這樣一本純手工大書,你每天是怎樣的工作狀態?
樑曉聲:我也不能作一個聲明:本人在寫長篇,請勿打擾。實際上聲明瞭也沒用,該接待還得照常接待。所以是默默地寫,擠時間寫,搶時間寫。有時,一白天沒洗漱,就那麼接待客人。客人一走,立刻執筆。這個過程身體自然糟糕。十個指甲都變形了,至今也沒恢復。還出現了鬼剃頭,三四處一元硬幣那麼大的禿斑。但我有韌性,有毅力。寫長篇也是對身體的考驗。我只能說,如果幹擾情況少些,會寫得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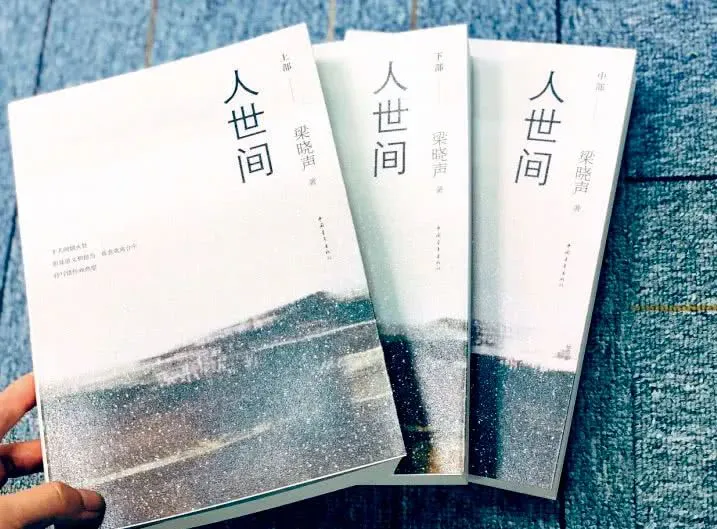
《瞭望》:這部書你寫得最動情的是哪些篇章?
樑曉聲:周秉昆父親周志剛在貴州山區看女兒的片斷;他與年輕工友郭誠的忘年交;他送小兒子去鄭娟家的片斷。我寫他時,內心充滿親切感,他身上有我父親的影子。寫鄭娟的老母親,我心肅然;寫周秉昆他們與曲老太太的感情關係,我心溫暖;他們去看望臨終的她,我心愀然;寫軍工廠老工人的死,國慶爸爸以及他自己的死,我心生難過。最後一章,哥哥去世了,嫂子改嫁了,周秉昆無意中見到了她,自己的內心也感情複雜。當然,還有周蓉與馮化成之離婚,我真不願那樣寫。但那時,他們的關係,已不由作家左右。
《瞭望》:《人世間》書中的人物名字比如周秉昆、周秉義、周蓉、國慶、德寶、趕超、春燕等等,似乎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時常見到的,你是如何看待和描摹筆下這些看似普普通通卻有血有肉的人物的?
樑曉聲:以前我曾多次說過,我是一個被友情簇擁著活過來的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未缺乏友情的溫暖。這種與普普通通的中學同學、知青好友的友誼,是更純粹的友誼,像極了周秉昆和他的朋友們的關係。前幾年冬天我回哈爾濱探家,返京的晚上,七八個老頭老太送我一個老頭,出租車司機奇怪,問明我們是中學同學關係後特感慨。我與某些普普通通的人的友誼,跨時代,極長久,我與他們喜憂與共。所以,寫起他們及彼此關係來,很親切,也很愉快。
《瞭望》:書中背景是共樂區,請談談你心中和筆下的共樂區與現實生活中的共樂區有什麼異同。
樑曉聲:如今共樂區還叫共樂區,那幾條與仁義禮智信連在一起的街名,還那麼叫。但髒街已不存在,破院已不存在,共樂區成了哈爾濱市一類街區,再也沒有人家冬天挨凍了。在《人世間》中,國慶因患尿毒症自殺;現實中,我的兩個弟妹也都患了尿毒症,但生活已不至於因而塌方。必須承認,現在城市變美了,乾淨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也今非昔比了。中國正在向好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將提高——我對此深信不疑。
《瞭望》:聽說你在出版《人世間》這本書時和出版社不提印數,這種背對市場的寫作姿態,是否可以說正是出於你對文學的執迷?
樑曉聲:好書不一定都在市場上以失敗告終,但創作的初心一開始就瞄準市場,那就真的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了。那是牛的狀態,也是為市場而勞役的狀態。“為道日損”,既然這樣也損,那樣也損,我便寧願為文學之道而損。在我看來,作家寫作,預先是不必別人投資的。我根本沒有印數要求,是為求得一種純粹。我的初心是懷著純粹之目的,向我所理解的現實主義致敬。正如我寫《父親》《母親》,是為了向自己的也向許許多多同樣的父母們表達兒女的感恩。
《瞭望》:評論家一致認為《人世間》是一部具有經典意義的現實主義作品,請談談你對現實主義的認識。
樑曉聲:真正的現實主義,不但要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還要寫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只寫深了前一點,固然會是好作品。同時可信地寫到後一點,則會好上加好。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狄更斯、莫泊桑、契訶夫等,他們都寫到了後一點。而只要寫到後一點,則溫度在焉。作家此作品無溫度,另外的作品必然有。魯迅也是如此,契訶夫也是如此。《第六病室》是陰冷的,卻也是有溫度的,體現在拉京院長身上。儘管他也被迫害致死,但這一人物身上熠熠生輝的人性之光,照耀全書。
今日之世界,絕非毫無溫度之世界;今日之中國,社會溫度受到空前重視;今日我所秉持的現實主義,首先是有溫度的現實主義,這不是指方法,而是指真誠。有此真誠,就會要求自己——客觀一些,再客觀一些;全面一些,再全面一些……
《瞭望》:你從一個起步之初就非常暢銷的作家沉寂下來到寫這樣一本百萬字鉅著,年紀也從十幾歲到了七十歲,寫作的心態是否有什麼不一樣?
樑曉聲:肯定是發生變化的。我已不再有通過文學博名獲利之念。文學和生活、時代使我成了作家,否則我亦不過是周秉昆。我該向文學、生活和時代恭恭敬敬地進行回報了。時不我待。都七十歲了,再不回報更待何時呢?
《瞭望》:你寫了超過半個世紀,這樣持久艱辛地在一個領域深耕,你抵達的是否是你當初的預想之地?
樑曉聲:前一時期,重讀《靜靜的頓河》《苦難的歷程》《父與子》《套中人》——非原著,而是精美的畫本;上世紀80年代買的,卻也不是小人書,而是三十二開的那種。繪畫風格各異,棒極了。因為喜歡,所以保留了三十幾年。重讀之下,抱憾難眠。創作《靜靜的頓河》那類經典,是可遇不可求之事。但巴扎洛夫、別裡科夫那類人物,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仍比比皆是,可我沒有自己的《套中人》,也沒有自己的《父與子》。
我已難達預想之地——從頭來過或許可能。但我的眼一直望向它,努力過了,接近了一步,算是欣慰吧。
我的文學之地與獲什麼獎已毫無關係。尺度在我心裡,並且我已明瞭。明瞭也是一種獲得,獲得就還想回報。總而言之,我欠文學、生活與時代的,我愉快於一次一點兒的回報,如回報親情、友情、愛情。
《瞭望》:從寫作之初到現在,你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樑曉聲:名利心漸少,創作虔誠心增強。創作一經印成書,便具有商品屬性。人家買滋補品,是為保健;買衣褲襪子手套,是為保暖。作品標了價,人家買了,還要花時間讀。作家認為自己的時間寶貴,讀者的時間就不寶貴了?於是會自問——你的書對別人到底有什麼買的價值、讀的意義?每這麼一問,不復再敢僅僅以博眼球為能事。讀者是分層次的,有一類專以咂低俗為偏愛,要與他們做切割。不論這一群體能鼓譟起多大的市場響動,都不取悅。
還要擺正文學的社會位置、作家自己的社會位置,文學不等於文化。在西方,宗教曾是文化長子,擔責撫慰世俗苦悶。在中國,文學實際上成了文化長子。價值觀在文化那裡,是思想;而文學通過形象體現和傳播思想。
文學只有在與其他藝術聯袂,形成啟蒙影響和作用時,才是它最功不可沒的方面。通常情況下,作家只不過是一種文化範疇內的職業,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敬業就好。敬業意味著要提高產品品質。
《瞭望》:你一直堅持的是什麼?
樑曉聲:用筆寫作,沒有使用電腦等寫作。這也談不上是堅持。只不過是笨。越笨越不敢換筆。我將克服怕的心理,爭取早日換筆。
《瞭望》:你探求和追尋的文學的意義是什麼?
樑曉聲:通常年代,文學有如下三種意義:一、雖然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雖然世界變平了,但實際上,大多數人與社會的複合面是有限的。文學使人瞭解更多種的人生。可引為鏡,照自己,以利於更加了解自己。某些文學中,有在現實生活中少遇的良師益友,許多人需要此種良師益友。
二、養成讀書習慣,對於當代人世是益事。而幾乎所有愛讀書的人,都是從讀文學作品開始的。文學像我們的長兄長姐,替我們標明路線,引我們進入書籍的殿堂。故,所有的讀書種子都感激文學。
三、在一切長輩和晚輩之間,特別是在父母和兒女之間,文學是最有益於增進深度瞭解和理解的話題。即使意見不同,也還是那樣。但吃喝玩樂的話題不能。話不投機,那就互生反感。對於有讀書氣氛的家庭,某些文學中的可愛可敬的人物,像不在籍成員,那是特好的感覺。
我以前的作品,也就那樣了。
我今後的作品,爭取達到這樣的自我要求。
《瞭望》: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你說“書籍像爐火”,你要用書回饋生活,在當今這個閱讀趨向碎片化的時代,你對文學是否依然抱有信心?
樑曉聲:是的。不是依然抱有信心,而是又重新恢復了信心。再強調一次,與個人作品獲不獲獎毫無關係,與個人創作前景怎樣毫無關係。我之信心,根據這樣一種展望——在未來三十年間,在全人類,特別是在中國,文學將如天女散花一般撒向民間。於是情況成了這樣,讀者與作者在某些人身上覆合,他們既是讀者,也許同時又是作者。某一年,忽有好作品產生,卻未必再是職業作家創作的,而是署著名不見經傳的人的名字。於是,文學曾經的神秘面紗被新時代的風吹走了,似乎只有成名作家才能創作出好作品的歷史會終結。文學在民間生根開花,彷彿《詩經》中的“風”那樣。
作品可能廣為流傳,但喜歡文學的人從來是小眾。即使在文學風光的世紀或年代,那也還是小眾。在別國也是那樣。我的信心建立在對這小眾的品質的細心瞭解之後。碎片化閱讀某時期會使這小眾更少,但也會使這小眾的品質更純粹,進而更優化。
我的眼看到,在中國,賴以成為文學種子的這小眾,正處於自然分化和優化之過程。不經分化又哪有優化呢?LW
刊於《瞭望》2020年第19期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訪樑曉聲:在悲歡離合中抒寫道義與情懷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