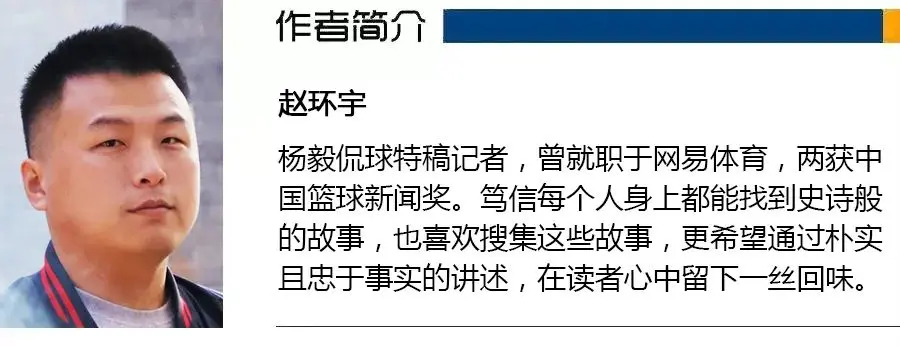
本文共6098字,閱讀約需23分鐘
4歲半送到美國特訓、一年光訓練費就30萬……北京的“球爹”圈裡,流傳著許多光怪陸離的故事。所謂“球爹”,就是指帶娃學籃球、打籃球的父親們,這裡所說的“娃”,指的是小學階段(U12)的孩子們。
第一次聽到“30萬”這個數字時,我先是感到震撼,然後默默在心裡計算:“平均每月2萬5,每週6250。”跟冰球相比,這樣的支出不過是“灑灑水”,但在籃球領域,卻是絕對的天文數字。
數字總是具有極大的衝擊力。崇尚工具理性的人會忙不迭地判斷它是否合理、劃算,也有人試圖透過火爆的市場去洞見國籃振興的蛛絲馬跡。不過,球爹們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邏輯。
▶
“失敗學”
上週日早上7點40分許,太陽剛剛躍出地平線,資深籃球媒體人老陳的車在我跟前停穩,他8歲半的兒子丁丁坐在車後排,隔著車窗向我打招呼,把手揮得飛快,臉上掛著跟老陳一模一樣的招牌微笑。
丁丁在2017-2018賽季CBA總決賽期間完成籃球啟蒙,今年開始接受系統的籃球訓練,已經能夠熟練運用左右手上籃,而且比賽經驗豐富,標準籃架、小籃架,三對三、五對五都打過,平均一年下來打個三四十場正規比賽不成問題。
“心情又好了?”我在副駕駛坐定,問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的老陳。“昨天回家就沒事了。”老陳樂呵呵地回答。
週六下午,丁丁是氣鼓鼓地離開球場的,他的球隊在那個三對三賽事中1勝1負,沒能打進前三。在關鍵的半決賽裡,丁丁和小夥伴們被對手“剃了光頭”。其實,比分被拉到0比8的時候,有的孩子臉上已經帶了哭相,我當時很怕他下一秒就會“哇”地哭出聲來。
輪到丁丁的球隊進攻,隊友在弧頂很難出球,一直站在底線錄像的老陳罕見地急眼了:“丁丁,要球!要球!”丁丁在慌亂中剛把手舉起來,球就從頭頂上飛出了邊線,失誤。老陳這下更生氣了:“你在想什麼啊?!要球去啊!”丁丁張了張嘴,想辯駁,卻似乎又無話可說,眼淚瞬間就掉了下來。
整個過程大約持續了幾秒鐘,他很快擦乾眼淚,繼續兢兢業業地貼身防守——儘管取勝無望。
那天下午的比賽開始之前,丁丁瞪著水汪汪的大眼睛,把一隻手舉到了老陳的面前,有根手指的指尖正在往外滲血。“小磕小碰都是經常的。”老陳側著臉對我說,手上卻沒停下,用一塊創可貼給兒子做簡單的處理。丁丁始終很平靜,沒有大驚小怪,也沒有哭鬧。
結果,這個堅強的小男子漢被老陳一聲怒吼“破防”了,沮喪的情緒一直延續到賽後的更衣室裡。
嚴格來說,那不是一間“更衣室”,而是球館裡的辦公室,靠裡的地方擺著幾把椅子和一些運動器械。前北京男籃後衛門維坐在沙發扶手上,以這支小球隊主教練的身份例行講話,丁丁別過自己寫滿了委屈的臉,賭氣般地告訴門維:“我在比賽中運用不了技術。”

門維是這樣回答他的:“你哭能解決事嗎?你哭一鼻子咱們比賽就能贏嗎?如果哭能贏比賽,不用你哭,我去哭去。輸了無所謂,但咱輸得知道輸在哪。以後搶球的時候能不能兇一點,能不能把人撞出去?”
他希望孩子們能“勝不驕敗不餒”,不能贏了就得意忘形,輸了就垂頭喪氣。講完話,他站起來,伸出手,招呼大家做一個互相鼓勁兒的動作。丁丁慢吞吞地把手搭上去,用最小的聲音喊了聲“加油”。離開球館的時候,丁丁把老陳甩開好幾米,連跟人說再見都有氣無力。
看得出來,這場失利再加上爸爸的斥責,對他打擊不小。
知名學者劉瑜前段時間有個演講爆紅網絡,她感慨說:“我們的社會充滿了成功學,但是卻沒有‘失敗學’。”其實體育,就是最好的“失敗學”老師,正如白巖鬆所說:“體育首先教會孩子們如何在規則的約束下去贏,接下來教會他們如何體面並且有尊嚴地輸。”
老陳帶丁丁打球的核心訴求有三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挫折教育,正確地面對輸”。許多球爹跟老陳一樣,堅信體育尤其是籃球,能夠補上“挫折教育”的關鍵一環,他們同時堅信,這對孩子將來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
“全世界帶你去學習”
與老陳父子會合之後,我們一行三人直奔順義某球館,丁丁即將在那裡參加BIYB聯賽(北京國際青少年籃球聯賽)U10組三四名決賽,他是隊裡最小的孩子,卻也同樣不可或缺。
那是一座投入使用不久的球館,一裡一外兩塊場地,幾十盞頂燈發出的光打在簇新的啞光地板上,映出許多巨大的光斑。斜對角各掛一個巨大的電子記分牌,高端大氣上檔次。
場邊圍滿了球爹球媽,有的只是淡定鼓掌,但更多的是全情投入——他們甚至比教練還急,恨不得把球搶過來替孩子上場。有個球媽,看到驚心動魄的地方,總是急得跺腳;有個球爹,眉頭擰成了麻花,拿著手機圍著場地溜達,時不時衝著兒子喊一嗓子:“你躲什麼呀?”“跑動!接球!”“籃板!籃板!”比賽中,有個球爹對裁判的某個吹罰不滿,在場地一角扯著嗓子喊:“你有孩子沒有啊,吹你家孩子你願意嗎,從背後推。”被其他球爹拽住。

“我之前啊,比他們還暴躁。”老陳湊過來對我說,眼睛並不離開手機,“這也是修煉自己的一個過程,你教育孩子,就應該教育自己,你想讓他改,根源就得自己先改。”
最終,丁丁所在的球隊以35比14大勝,隊員們都獲得了一枚設計精美的銅牌,丁丁拉著老陳在場邊拍了好幾張照片,老陳說要把照片發給孩子的爺爺奶奶。不過他小時候可沒這待遇,打球都是偷著打,進校隊都不敢讓家裡知道,直到拿了區冠軍才怯生生地把打球的事告訴了父母。

賽後,球爹們例行聚餐,我沾了老陳的光,飽飽地蹭了一頓午飯。聚餐的地點選在離球館不遠的一家“平民烤鴨店”,兩個相鄰的包間被打通,教練和球爹們坐一桌,球媽們和孩子們坐一桌。菜上齊之前,老陳偷摸跑到前臺把賬給結了,他說經常有家長這麼幹。
以孩子為紐帶,球爹們構建了一個只談籃球和孩子的特殊的朋友圈,你會發現,有許多網絡論壇上熱議的話題,被球爹們搬到了這張其時已擺滿殘羹冷炙的餐桌上。比如,能仁家商和清華附中到底誰更強?
“能仁家商學的是日本福岡(第一高中),日本福岡學的是維拉諾瓦(大學),完全照搬過來的。”身型魁梧的教練侃侃而談,“你看人家日本福岡那個協作,身體跟連著鐵鏈似的,怎麼移動都不會超出那個距離。”
球爹大徐想起了陪兒子Martin到日本參加訓練營時的情景,搭話道:“人家根本就不運球,全是傳切,跟日本足球似的。”大徐說,光這一個訓練營就耗資27800。之後又經香港到深圳參加比賽。一年下來,投入有小20萬。他跟兒子有個約定,只要兒子堅持打,他“可以全世界帶他去學習”。
他發給我一個賬單,上面列明瞭幾項開支:日本營27800、從零開始9280、60次常規課15800……而這僅僅是他花在同一家培訓機構的錢。
於是引出一個話題:培養一個U12球員,到底需要多少錢?直接的開銷包括訓練費、營養費、裝備費、比賽報名費,如果要去外地比賽,還得額外加上不菲的交通費和住宿費。其中,訓練費是“大頭”。
我們可以總結出兩個大致的趨勢:不在校隊的比在校隊的花錢多,水平越高花錢越多,“到了一定階段,不投錢就走不上去,因為那時打的已經不僅是場上的東西了,體能、康復、營養,哪一項跟不上都不行。”體育經紀人馬佳——她是丁丁隊友大林的媽媽——告訴我,“現在已經不是多少年前了,一把雞蛋打在牆上,沒碎的就是冠軍。”
能力超出同齡人之後,培訓機構的大課就不再能滿足球員們的需求,他們必須進行特訓。球爹們給我舉了幾個例子:街球手趙強,2小時1000-1500元/人;“花式籃球第一人”韓煒,2小時500元/人;外籍訓練師每小時1000元/人。
一年20萬、30萬是比較誇張的數額,我那天所接觸到的球爹們絕大多數的支出,都在10萬以內。比如丁丁的隊友小齊,一年學球、打球要花掉“七八萬”。再比如翠微小學校隊的小黃,雖然週一到週五跟校隊練,但為了強化個人技術,他的爸爸給他報了特訓班,再加上寒暑假的集訓,總共需要“四五萬”。即便是在圈裡擁有豐富人脈的老陳,也要花掉兩三萬。

而這還僅僅是有形的成本,無形的時間成本就更加難以統計了。
丁丁被老陳訓哭的那個下午,我在場館外的寒風中跟全職爸爸王一飛聊了20多分鐘,他的兒子鈞鈞跟丁丁是球友,最近經常在一起一打一。自從鈞鈞上小學,王一飛就辭掉了保險公司的工作,全職照顧鈞鈞飲食起居、陪伴鈞鈞成長,家裡的經濟重擔則由鈞鈞媽媽一肩挑起。
王一飛不光要做飯、接送鈞鈞上下學、輔導作業,還得陪他打籃球,每天雷打不動的2-3個小時。從下午3點半到晚上10點半,大約7個小時,王一飛把時間全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他是學經濟的,不止一次跟我提到一個詞:機會成本。“時間用在這兒了,別的就幹不了了。”
他的“瘋狂”不止於此,有時候,他甚至會跟學校老師請假,上課時間帶鈞鈞去練球。這不禁讓我想起小齊的爸爸在“平民烤鴨店”說過的一句話:“學習別拔尖兒,拔尖兒孩子也累得慌。”他們是家長中的異類,卻不是北京家長中的異類。
言歸正傳,用一個完整的勞動力陪孩子打球,我問他值嗎?
“值啊。”王一飛的回答很乾脆,幾乎是不假思索,繼續笑著——他的笑幾乎沒停過——說道,“兩個人總有一個要為了孩子做出犧牲。甭管成績怎麼樣,就這幾年陪伴孩子的時間,過後想想,會是非常寶貴的記憶。孩子的媽媽很羨慕我,因為這些事情她做不了。”
▶
“陪他就好”
讓我們把目光再拉回到喧鬧的烤鴨店。
後來,聊天的話題轉向體育在當下教育體制中的尷尬處境。“中午老師們要搶課,孩子們沒有運動量呀。”“體育老師不讓孩子跑1000米,校長還說做得對。” “當然做得對,不然跑出問題來你負責?”“體育老師的要求就6個字,‘走起來,別崴腳’。”一位球爹的發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在球爹們聊得起勁的時候,孩子們也開始了屬於自己的遊戲,尖叫著從一樓追到三樓,又從二樓跑回到包間裡,從椅背與牆壁的縫隙間鑽過去,繞著餐桌追逐打鬧。不知怎的,有兩個孩子開始在小夥伴們的起鬨聲中,像橄欖球運動員一樣斜著身子,鉚足了勁用肩膀去撞對方的肩膀,誰也不肯服誰,直到家長們厲聲制止才停手。
丁丁喜歡跟隊友們對撞,但他在學校不敢這麼做,因為“一撞就告老師去了”。通過打球,丁丁結交了許多朋友,儘管大家平時散居在城市的各處,但一見面就格外親密,擁抱,模仿NBA球員用Dab的方式打招呼。
“咱們所謂的發小,他們是通過打球得到的,甚至有種戰友的情誼在這裡邊,可以陪伴他一生。挺好。”王一飛說。很多70、80後父母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圈,都是以父母的單位為圓心,以父母的工作關係為半徑的。家庭這一基本單位之上,是“大院”,院裡都是父母同事家的孩子,大家從小玩到大,但是現在的孩子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球場上的感情,正如王一飛所說,還有戰友情在裡面,他們一起在場上流過汗甚至流過血,你為我掩護,我為你補防,“一起扛過槍”的情感紐帶,是課堂上不存在的。
“結交朋友”,是大徐花20萬供孩子學球的三大訴求之一,另外兩個訴求分別是鍛鍊身體、培養自主能力。再加上前文提到的“挫折教育”,我那兩天接觸到的所有家長的訴求,都不超出這四個範疇。沒有一個家長的目標是職業籃球,充其量是CUBA。
——或許曾經有過將孩子送進CBA的念頭,但最終也不得不坦然接受孩子的平凡,這是絕大多數家長都要經歷的過程。
小學畢業之後,學業壓力陡增,王一飛還能請假帶孩子打球嗎?到時候面對的,或許只能是“二選一”的困境,“對我們來說,還得面臨來自家庭的壓力,比如孩子的媽媽還是希望他走學習,到後面(學習和打球)是不可調和的。真要以後是那塊料了,再說。”
如果僅以能否進入CBA或CUBA論英雄,這些孩子的絕大多數會成為“分母”,他們走的,是一條大概率沒有結果的路。
“CBA每年也就400多個人可以打,進CBA比進清華北大概率還低。”馬佳說,中國男籃兵敗2019年世界盃之後,金字塔頂的哀鴻遍野和金字塔底的欣欣向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感,令她印象深刻,“孩子和家長的熱情沒有受到影響。”
“達不到塔尖就不從事這項運動了嗎?我們是在揹負著整個中國籃球的責任在從事這項運動嗎?當然不是。因為這個運動本身是一個很好的運動。”老陳告訴我,“就像足球,喜歡踢就踢唄,不是我愛這運動,就必須在世界上最牛逼。你愛這運動,那就去從事它。”
換句話說,家長們送孩子打球時不會考慮“國籃崛起”這樣宏大的命題,國籃崛起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動機。家長們所看重的,不是這條路的終點是什麼,而是陪伴孩子走過這條路時看到的風景。
“體育對我們來說,不是競技,而是教育。那些淘汰的是悲哀嗎?實際是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那個三對三籃球賽的場邊,老陳指了指丁丁,對我說道,“這天賦打不了職業的,它不是給中國籃球培養球員的,但它是培養球迷的,未來這些孩子,哪怕不打籃球了,也會是中國籃球最忠實的擁躉。”

陪伴,是球爹們經常提及的詞彙。這是一個父母與孩子相互培養、相互發明、相互改變的過程。拿老陳來說,他邊帶孩子練球,邊修煉自己的性格,從暴躁到相對沒那麼暴躁。同時,他也在逐漸找回自己對籃球的熱情。
“我好久沒打球了,跑不動了。”我摸著自己的肚腩說。
老陳拍了拍我的肩膀,顯得語重心長:“等你有孩子了,你的熱情和潛力就釋放出來了。”
他將“孩子練體育”比作生活的興奮劑,“我40多歲了,生活平淡了,但是陪孩子打球的時候,我會把情緒投入進去,看孩子贏球,比看中國籃球進了世界前八我還開心。”
“在我們這個年紀,上有老下有小,趁著還有精力(趕緊發力),別等你想發力了,卻沒有精力了。你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給自己一個第二次成長的機會,痛苦和快樂都要一起經歷。”老陳說,他把籃球當作一種“精神需求”。
王一飛給我講過今年暑假裡發生的一件小事。
那天上午,父子倆的訓練從7點持續到9點。之後王一飛提議就近爬個香山,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2點,既熱且累,“休息休息吧。”王一飛跟鈞鈞說。可是被拒絕了,“爸爸,我想練球。”王一飛事後想想,支撐他走下來的,可能就是這種非常感人的瞬間。
我似乎可以想象:大汗淋漓的父子倆,如同鏡像,孩子映照著父親的過去,父親折射著孩子的將來。
“現在我一個人還能解決所有的後勤、陪練,還要做父親的角色,陪他玩、看書。往後也只能做陪伴了,等他到一定水平了,跑個戰術啥也不懂、啥也說不上來的時候,陪他就好。”王一飛說,“我以陪伴的目的為開始,以陪伴的結果看他長大。”
陪伴,功利心含量極低的陪伴。長著一個將軍肚的老徐說,如果有一天兒子在籃球道路上掉隊了,他也能“坦然接受”,“我深知咱們不是運動員家庭,我看中的是孩子通過籃球鍛鍊體魄。”
在一次次驅車趕往賽場的路上,在一次次筋疲力盡的下訓之後,在陪伴中,孩子的成長不再是捉摸不定的東西。比如老陳近來就發現,丁丁開始對他教的東西有所質疑,開始“不聽話,偷偷吃東西”,他的人格正在逐步獨立,老陳將這稱為“思辨能力的發育”。
▶
“你比你爹上道”
烤鴨店的聚會結束之後,老陳開車從順義趕回朝陽區,他交代丁丁看圍棋課,經過討價還價,丁丁獲得了5分鐘寶貴的看比賽的時間——當代小學生都很忙碌,他們的時間像成年人一樣被切割成了碎片,車上吃飯、車上學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這是我最不緊張的一場比賽。”丁丁突然開腔。
老陳分析說:“因為昨天的比賽對你心理成長幫助很大,今天你敢於去主動對抗、主動搶,雖然沒搶下來,但重要的是你得去搶,你總有一天會搶到。”
兩天前,老陳更新了朋友圈,說是教練體能訓練加量,丁丁折返跑輸給了比他小兩歲的夥伴。老陳看著垂頭喪氣的兒子,十分心疼,試圖安慰:“辛苦丁丁。”結果,丁丁眼望星空,緩緩地說:“不用這麼說,我又不是給你練的,是練給自己的。”
“行,小夥兒,人生不易,你比你爹上道。”老陳寫道。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北京球爹,一場不看終點的競賽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