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絲綢之路,承載了歐亞大陸3000年的交流史,是改變世界文明與發展的一條路。
研究絲綢之路的專家與學者有許多,香港城市大學原校長張信剛教授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代表之一。他對“一帶一路”各區域的文明演變與發展、國家興衰存亡等有多年深入研究,並用腳丈量這張地圖,進行實地尋訪。在新著《文明的地圖:一部絲綢之路的風雲史》一書中,他將所學、所聞、所感融入絲綢之路的風雲史中。個人視角下所展現的“大文明觀”,照見了歷史的印記與未來的晨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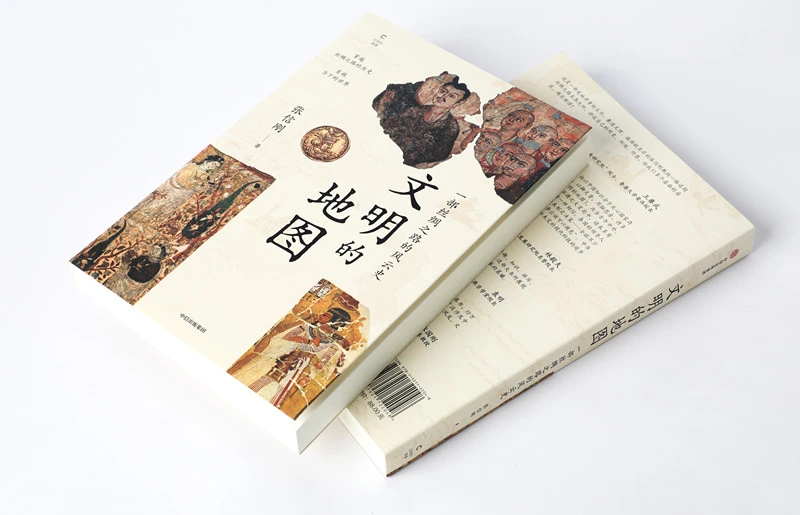
《文明的地圖》書封,中信出版集團
一條文明交融之路
上書房:2007年夏,您在香港退休後,探索絲綢之路和歐亞大陸的文明交流成為您的“新專業”。我注意到,您先是學土木工程,後來又學了生物醫學工程。您與絲綢之路是如何結緣的?為何目光落到文化研究上?
張信剛:我在小學四年級時就從課本上讀到了班超投筆從戎到西域建功的故事。上中學時,父親告訴我,歐洲人和日本人對中國新疆、蒙古和中亞地區很感興趣,不少學者都曾實地考察張騫所開通的絲綢之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絲綢之路”一詞。從那時起,我便對這條路抱有一種浪漫的情懷和無限的憧憬。
中學時我對文科興趣比較濃,但拗不過時代潮流,大學報考了土木工程。讀博士時,我選擇了生物醫學工程。但以後多年我在教學研究之餘也會經常寫一些人文和社會方面的文字。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有人說我是“理工男”,是用理工思維講述歷史和文化,這個需要讀者去感受。

絲綢之路沿線:埃及尼羅河上遊的菲萊神殿一角,修建於託勒密王朝時期
上書房:“絲綢之路”這種說法靈動而形象,它是從何而來的?
張信剛:在這條道路最早形成甚至是非常興旺的時候,還沒有提出相關概念。“絲綢之路”的說法最早是德國一位地理學家經過實地考察後在19世紀提出的,他認為,絲綢的貿易曾經是歐亞大陸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因而將這條路稱作“絲綢之路”。
其實,中國在多個世紀裡對外往來的主要通道就是絲綢之路。張騫出使西域,帶的很多物品中,主要以絲綢為主,這是中國的特產。絲綢逐漸向西傳播,一直傳到羅馬帝國。當時羅馬上層人物覺得穿絲綢衣物顯得身段好,夏天又涼快,特別受女士喜愛。正是由於中國絲綢對西方的影響,希臘早期將中國叫作“Seres”,就是“絲”的音譯。
人類歷史的地理宿命
上書房:用現在的話來說,絲綢之路是一條交通網。據您的觀察和研究,古代的遠程通道為何選中了它?
張信剛:任何人要創造歷史,都不能脫離自己的地理環境。1萬年前,幾大洲的人類都還沒有進入文明狀態,所以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地方發展得很快、很好,有的似乎還在原地踏步。因為地球的地理環境偏愛亞洲和歐洲,所以美洲、非洲、大洋洲“輸在了起跑線上”。
其實有幾個原因。歐亞大陸上有好幾條東西向(大約相同緯度,氣候類似)的交通路線,也有豐富的動植物品種。這有利於農業的發展和工具、技術的傳播。其次,歐亞大陸上有不少可以被人馴服的大型動物,比如牛、馬、驢、駱駝等,幫助人類進行長途運輸和貿易,這也大大增加了歐亞大陸的居民彼此學習的機會。
反觀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亞,陸上交通主要是南北向,要經過不同的氣溫區,對人的來往和農業物種的交換和移植都不利。而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許多動物都無法被馴服,比如非洲大象、斑馬、犀牛等,不能成為拉車馱重的動物。
而且,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原住民都是4萬年前從印度尼西亞渡海過去的,此後海平面升高,水道變寬,直到18世紀英國人到達那裡之前,他們都沒有與其他人類交往的機會,也沒有可用的大型動物,只有袋鼠為伴。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文明落後的原因歸結於人們的能力弱或者思想落後等,畢竟各大洲、各區域之間,大家所處的地理環境不一樣,腳下的路並不一樣,有的筆直而平坦,有的則是崎嶇難行,因此文明才有了不同的發展。

絲綢之路沿線:伊朗伊斯法罕著名的33孔橋
上書房:歷史上,許多人走過這條絲綢之路,有商人、僧侶、士兵、百姓等。在您眼中,哪些人是絲綢之路上的“信使”?
張信剛:第一個想說的是西漢的張騫,沒有張騫就沒有我們所說的絲綢之路。可以說,張騫是中原第一個瞭解到在沙漠和高山的那一邊還有興盛文明的人。絲綢之路的確是張騫兩次從西域回來之後開闢出來的,此後許多商人都沿著張騫的這條路線行走。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實現了真正的文化交流。物質上,張騫帶回汗血馬等優良馬種。另外,我們熟悉的一些農作物,比如石榴、胡桃、胡麻、胡豆、胡瓜等也是他回來之後才逐漸被移植到中原大地的,同時中原的絲織品和鑿井術等也傳到歐洲。文化上,經過絲綢之路,印度的佛教、希臘的塑像藝術等都傳入中國,對後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再比如鳩摩羅什。和從東向西走的張騫相反,他是從西向東走。他將《金剛經》《維摩詰所說經》等佛經翻譯成漢語。我們很熟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他翻譯的。
第三個重要人物是玄奘。玄奘去過很多地方,在印度的那爛陀住了十餘年,又花了5年的時間遊歷大半個印度和中亞各地,瞭解各地的風土人情。他回來後寫了一本《大唐西域記》,這本書對唐朝在西域的擴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奘本人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也是很大的,在印度的國會裡專門有描繪玄奘西行的畫像。
歷史和現實在行走中碰撞
上書房:沿著絲綢之路,您也去過不少國家。“行萬裡路”和“讀萬卷書”帶給您的感受有何不同?
張信剛:讀萬卷書和行萬裡路,都很重要。讀萬卷書,開闊眼界,正如杜甫所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明代的徐霞客遊歷於山川湖海,是行萬裡路的典型代表。我認為,讀萬卷書和行萬裡路有一個共同的要件,就是保持一顆好奇心,而且還要有目標、有意志力。
上書房:說一說您在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旅行經歷吧。
張信剛:我初次踏上絲綢之路是1978年由西安去寶雞,即絲綢之路最東端的一小段。真正進入漢唐時代的西域,體驗絲綢之路的風情是在1987年夏天,我和妻子從蘭州穿過河西走廊到敦煌,再經吐魯番、烏魯木齊到“絲路明珠”喀什。

絲綢之路沿線:土耳其特拉布宗蘇美拉修道院
記憶最為深刻的一次旅行是2017年5月,我去土庫曼斯坦和伊朗。我先到土庫曼斯坦遊覽,最後兩天在東部的馬雷度過,這裡曾長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我在馬雷包了一輛車,在幾乎是沙漠的地區行車大約3小時後,到達土庫曼斯坦的邊境禁區。車不能進入。於是我下車拖著重重的行李步行到土庫曼斯坦的邊檢站辦出境。出境後發現,原來土庫曼斯坦的邊檢站和伊朗那邊的邊檢站之間還有一個緩衝區,又拖著行李走,才能真正進入伊朗領土。在那裡乘上了一輛穿梭於邊境線與邊檢站之間的小巴,但是我身上只有美元,還沒來得及兌換伊朗貨幣,司機堅持不用伊朗貨幣付錢就不能上車。結果是一位好心旅客為我付了車費。
這次旅行讓我感受到,曾經長期是絲綢之路上的繁華都市馬雷(木鹿),經過歲月的洗禮,如今只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小城,附近幾個10世紀前後塞爾柱突厥人留下的清真寺和陵墓還在,但周圍只有荒涼的山丘。曾經,地理選擇了馬雷;如今,幾乎被歷史拋棄的馬雷正在等待絲綢之路新經濟帶的到來。
上書房:行走的過程中,會有一種歷史和現實在此交融的感覺?
張信剛:是的。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這種感受特別明顯。它是世界上唯一跨越歐亞大陸的城市,土耳其曾是古絲綢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地區。在伊斯坦布爾行走,可以感受它的迷人之處———地理、社會、思想上的複雜多樣、與眾不同,需要慢慢探索與品味。
絲路文明的新意和生機
上書房:您曾用杜甫的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形容絲綢之路的變遷。可以具體說說嗎?
張信剛:古絲綢之路曾經輝煌一時,從公元16世紀起,隨著海上航路的開通與繁榮,往日繁忙的陸上絲綢之路漸漸淪為世界上最為閉塞的地區之一,頗有“落日照大旗”的蒼涼。然而,到了今天,由於交通工具與通信手段的發達,比如正在建設的“歐亞大陸橋”,這些地區重新受到世界的關注。舊時絲綢之路被賦予了新意義,我體會到,“馬鳴風蕭蕭”有了新的生機。
上書房:新絲綢之路的發展,我們需要注意什麼?
張信剛:“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是時間的藝術。目前來看,我們的人才儲備還不夠,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瞭解的人太少。人類不同文明幾千年的接觸過程中,第二次並且是真正的全球化就在我們手中,千萬不要讓這個好機會從指縫裡溜走。
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還是經濟與文化並進。唐代時,日本人、高麗人、粟特人等都願意來中國唸書,許多人還在中國落戶。我們現在還遠沒有達到這個水平。

絲綢之路沿線:伊本·白圖泰故國首都(今摩洛哥菲斯)
上書房:在和世界文明的交融中,您認為中華文明的內核是什麼?
張信剛:中國人普遍是中庸而內斂的。在古絲綢之路的發展和融合中,許多地方的人彼此交融,有些地方消亡迭代,已面目全非。而數千年來,中國的語言和文字都有穩定而牢固的基礎。
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具有連續歷史的文明體。今天任何兩個屬於中華文明的人,都能用同樣的語言和文字彼此交流。今天的初中生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讀陶淵明的田園詩,都能夠欣賞,這本身就是世界唯一的,是值得我們自豪的,這也是我對未來的信心來源。
中國人比較看重“致中和”與“平衡”的概念。這個“中和”,也是指做事不要過度。另外,中國文化講究整體的平衡,心有大局,不走極端。中國人也講究辯證思想,比如否極泰來、苦盡甘來、居安思危等,這些對於人生都是有益處的。
文化對每個人的自我認知非常重要。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我”是來自一個什麼樣的體系很重要,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可能就會迷失自我;當他知道“我是誰”,他會有動力、有信心,而這個信心和動力與自己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頗有關係。

埃及首都開羅近郊的獅身人面像,後面是最古老的吉薩金字塔
上書房:今天,科學與技術將人類社會帶入DNA改造、幹細胞、電子商務和5G物聯網的時代。您又如何看待科技座標軸下的文明?
張信剛:我們所說的文明,其中一個維度是物質文明。不種植水稻,哪有糧食?蓋不起城牆,哪有城市?從農耕文明和畜牧文明,到工業社會、科技與互聯網,這些都推動了物質文明的發展。
文明的另一個維度是精神文明。人是有思維、有感情的,這就決定了人有心靈的需求和歸處,再豐富的物質也無法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在每個人的心底,哪種生活更快樂呢?或者說,人類進步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才是整個人類文明所要解決的問題。
當人太忙碌的時候,走路、坐地鐵、吃飯,都只顧著埋頭看手機,這樣的情況下,何以談心靈的感受和滿足感?如何能體會王維所說的“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感覺?當物質文明豐澹到超過人類生存所需時,其實會影響心靈的感受。如果我從小是看著手機長大的,就不會說“讀萬卷書”的好處,大自然、音樂、文學、詩詞等都是滋養心靈的方式,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也應該用合適的方式安放心靈。
我想和年輕朋友說,不要讓碎片化的信息掌控你的生活,乃至塑造你的人生觀。多讀書,多行走,世界很廣闊,要敞開心胸接受和享受它。
(文內圖片由受訪者提供;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唐代時日本人、高麗人來中國唸書落戶,因為這條世界之路,中國的機會又來了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