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青年一代的焦慮引發了廣泛的關注。相比於985中自嘲為“小鎮做題家”的高材生、在“績點為王”規則中的清北精英,“二本學生”在各類社會範圍內的討論中常常淪為“沉默的大多數”。
《我的二本學生》則將目光投向了他們,作者黃燈用她曾教過的二本學生們鮮活的經歷,訴說這批年輕人在時代變遷下的困惑與失落,焦慮與希冀,思索時代環境與青年發展之間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生存境況。
新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我的二本學生》的作者黃燈,一同回顧這本書、這個人、這一年。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劉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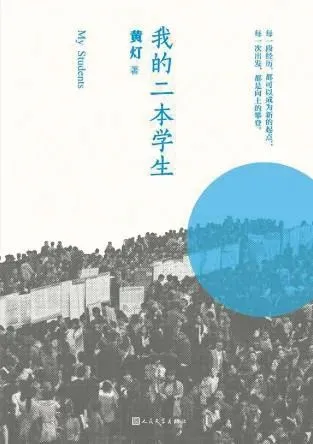
《我的二本學生》
作者:黃燈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8月
01
這本書
“相比理論的誘惑,我更想寫具體的人”
新京報: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是對學生自述的大量呈現,理論分析部分相對較少。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寫作方式?
黃燈:關於本書的定位,我在序言第一句就講得很清楚——這是一本教學札記。我在寫作的時候,被無數的想法和無數年輕人的形象、命運變遷所包裹,我想表達一種建立在經驗之上的複雜圖景、和一種基於直覺的觀察。
因為接觸的學生個案極為豐富,學生差異極大,我沒有辦法窮盡我教過的所有學生,這就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學術性的專著式寫作。從方法論而言,我也無法統計所有孩子的具體狀況,在證據欠缺的情況下,任何結論都是不負責任的。但我完整目睹、陪伴了80、90後兩代年輕人的成長,我知道很多孩子成長的故事和秘密,和他們有深入的交流,這是我的優勢。
任何一種寫作都有侷限性。相比理論的誘惑,打動我的是學生命運的流轉。當然,理論的觀照和對社會的透視,也是我寫作過程中隱秘架起的X光機,但從這本書的定位出發,我還是竭力避免生硬的理論介入,只是在合適的時候,趁機表達自己的觀點。
這是一本不完善的書,是一本侷限性很強的書,但也是一本誠實、節制,嚴格遵循非虛構寫作倫理和寫作要求的書。正是因為它的誠實品格,才接通了很多人的共鳴情緒。

黃燈,湖南汨羅人,學者,非虛構作家,現居深圳。著有《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曾獲“琦君散文獎”、“第二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非虛構主獎、深圳讀書月2020年度十大好書、搜狐文化2020年度好書等,入選《環球人物》2020年度面孔。
新京報:有評論認為,過多展開學生的個例,讓本書探討的一些有意義的問題淺嘗輒止,使得全書顯得比較零散,缺乏對問題的系統、深入的洞察。你怎麼看待這些批評?
黃燈:站在讀者的角度,可能會有這種想法。站在作者的角度,寫作者只能依據他所看到和掌握的材料來書寫,不能有半點越界。
我的寫作是基於我在廣東F學院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上課(公共課偏多)、當班主任、導師制帶學生這些繁瑣的事情,這種結構的確定性,使得文本無法獲得充分、系統、深入的討論空間,加上脫離既定素材的討論又會顯得遊離,我只得割捨。更重要的是,學生的成長因素特別複雜,很難和各種必然、偶然的要素建立因果關係。我既然選定了非虛構這種限制性極強的寫作方式,記下他們的成長經歷,是我最能把握、也最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我得承認,造成這種狀況,和自己不成熟的寫作有關。我還沒能處理好材料的誘惑和問題指向之間的關係。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與自己教的二本學生相比,“重點大學的孩子,仍舊以最古老的方式,端坐在圖書館閱讀泛黃的紙質書籍”。聯繫高校“學術KPI”的現象,你怎麼看待頂尖高校因為過度競爭的焦慮,“容不下安靜讀書的書桌”?
黃燈:我在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重點高校都待過,在這些學校裡,我總能看到不少孩子還是以最傳統的方式認真讀書。那個時候,我就感慨,二本院校學生和他們的差異,可能是圖書館和高質量學術講座的差異。當然,重點高校出現“績點為王”的狀況也是真實的,但有不少學生還是在安心讀書。
在全球化出現挫折和分化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大家都在共同承受這一後果。從這個層面而言,我從來不認為我僅僅只是寫了二本學生,他們背後實際上站著更為龐大的年輕群體。
02
這個人
“社會轉型期的親歷者、見證者和介入者”
新京報:《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後,獲得了非常多的關注。你怎麼看待它的走紅?你的生活有發生什麼變化嗎?
黃燈:這本書並不完美,它的影響力主要來自話題的重要性,來自社會對年輕人命運的關注、思考,以及對轉型期社會走向的探索。我的寫作,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和切口,便於大家討論問題。
除了要接受採訪,我的生活沒有太多改變。有意思的是,採訪我的記者,95%是年輕人,是80後,90後。他們大部分都是名校畢業,不少有海外名校留學的經歷。但他們普遍對二本學生的話題感興趣。採訪之餘,我們會共同探討年輕人的命運,會探討社會、時代和年輕人的關係。
新京報:你在書中也提到“導師制”的實踐。你不僅對文學課堂進行了精心的設計,還非常注重和學生的交流。這是一種有別於通行於目前國內高校體制化、標準化教學的“精耕細作”。現在還在堅持嗎?“導師制”的意義是什麼?
黃燈:我進行的“導師制”實踐,是基於師生互信所建立的一種十分鬆散的“君子協定”。換言之,就是“學生願意學,老師願意教”,沒有任何考核目標,也不進入學校的任何評價機制,當然,也沒有經費支持,所以,它算不上“精耕細作”,純粹是“業餘施肥”。
我在廣東F學院的時候,嘗試“導師制”很多年。最近因為工作變動,調往了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暫時還沒有施行。
“導師制”也說不上有太多意義,就是通過師生的協調和信任,去獲得一種真正的大學生活的體驗,獲得一種因為思考和閱讀帶來的樂趣,讓大家擁有一個交流和提升的機會。
新京報:2016年,你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曾引發廣泛討論。鄉村書寫一直是你關注的領域,你覺得那篇文章和《我的二本學生》之間,有怎樣的關聯嗎?
黃燈:兩者之間確實存在關聯。我寫農村兒媳這篇文章的動因,來自對年輕的侄子侄女命運的憂慮,他們作為留守一代長大了,但他們甚至連重複父輩的命運都不可能。後來寫完《大地上的親人》,我腦海中始終盤旋一個問題:那些比我年輕十歲、二十歲的晚輩,如果考上了大學,會如何?而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恰好回答了這個問題。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專訪《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看見中國普通年輕人的命運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